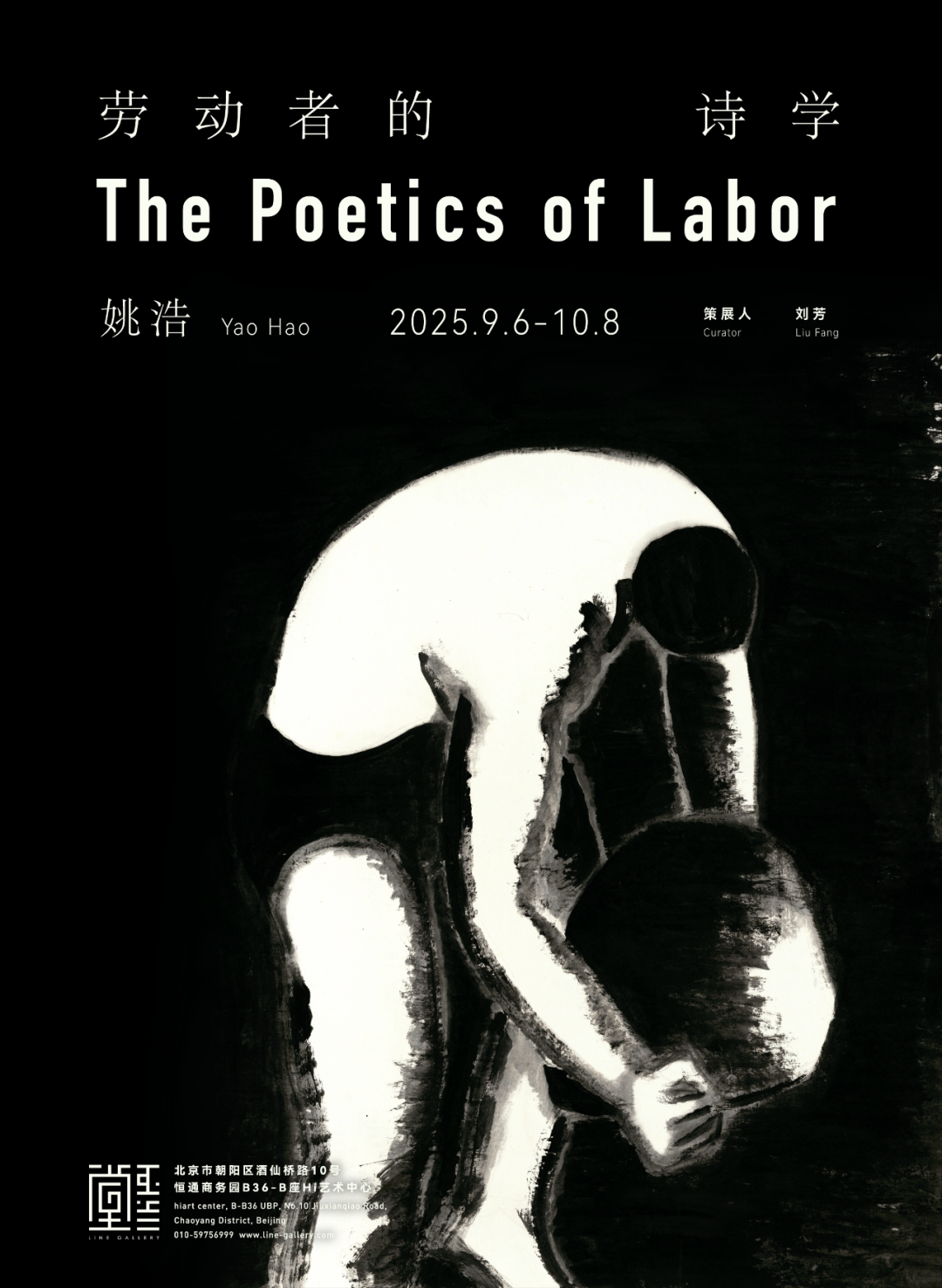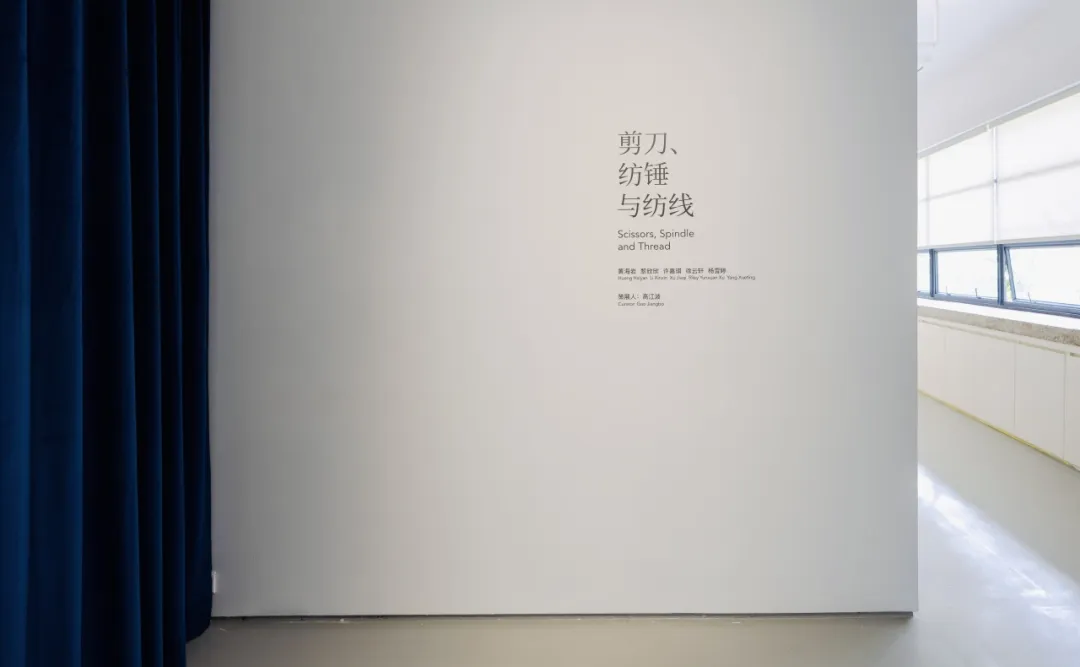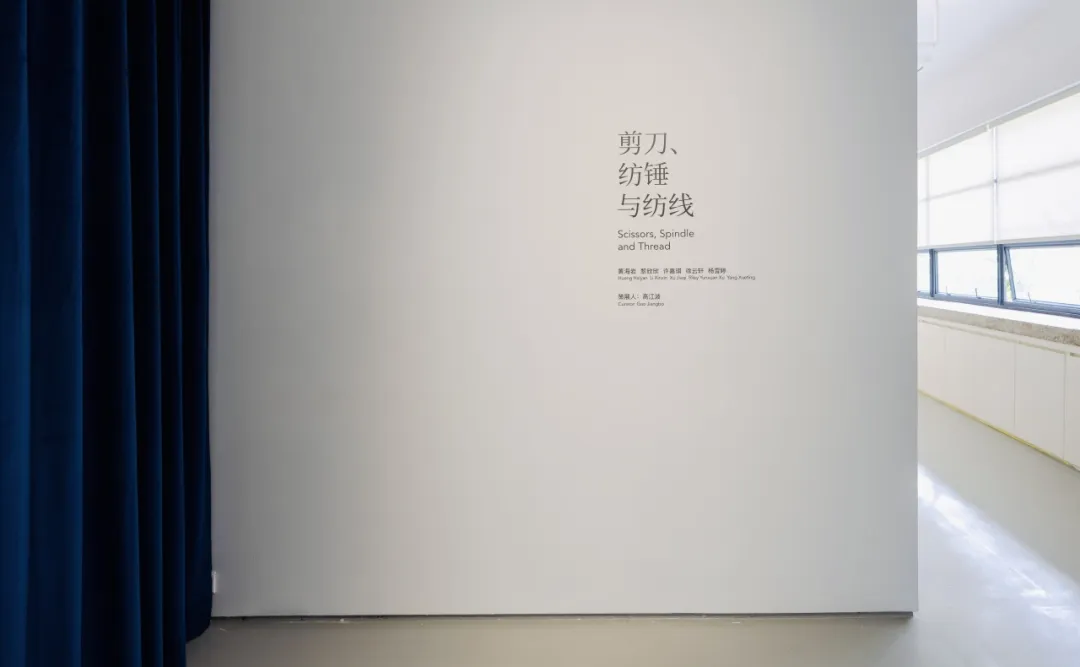
写在前面:
首先我希望这篇关于嘉琪的文本能更好地回答藏家好朋友Y的疑问,“为什么要用希腊神话的话题概括展览?”。虽然我已经忘了当时我怎么回答了,但彼时她并没有认可或被解惑。这让我意识到在策展实践中的留白,也有滑向“空泛的自我陶醉”的危险。当然,策展归策展,这篇文章并不完全是策展的延伸。也有作为文化研究和美学批评的功能,但推导逻辑和文风均以我自己的工作习惯为主,并接纳任何驳斥和反对的声音。
我想从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开始聊。维特根斯坦曾经提过一个好玩的假设:“哪怕狮子会说人话,我们也听不懂它说什么。”乍一琢磨可能觉得没有道理,但仔细去想,狮子在野外因为自身的生理特性和习性,并不与人类共享任何生活。因此狮子“说什么”和“如何听懂”就变成了要弄清楚狮子的生活和为什么要说人话的动机问题了。一种完美的答案是:或许它本来就是一个人变的。

许嘉琪(以下简称QQ),她的工作呈现出明显的隐喻拓扑结构。例如《哲学玫瑰园》中,“被立体的脊柱剑劈开的爱心表情包”和“墨丘利之泉”都共享着一种关于“维度跳跃”的转化隐喻。就像月亮和船都共享一种“弯曲”的隐喻或感受,她自述中讲到“剑与脊柱再次缠绕、逻辑被情感弯折,守护与暴力同体。”因此两者的组合就像是矛盾的两端、相互转化又异体同构,就好像内外相连的克莱因瓶或者莫比乌斯环一样耐人寻味。“墨丘利之泉”是符号,“脊柱剑”和“爱心”是现象、能指。在拉康的语言学体系里,符号对应的意义是单一的,但能指所对应的意义永远是滑动的,比如“猫”这一事物在不同语境下时而读作“喵喵”时而滑向“哈基米”的情况。我们在看到QQ这件“脊柱剑爱心桌”在蚀刻了“墨丘利之泉的符号”后,顺手也将作品的材料(水泥颗粒感)、颜色、甚至尺寸纳入了作品内部丰富的能指集当中,让意义在上述能指要素间不断流转和生成,暗合了QQ本来的观念,物质能量相互转化,也在转化的缝隙中生成。

许嘉琪 / Xu Jiaqi
哲学玫瑰园 / Philosophy Rose Garden
2022
亚克力、树脂、仿石涂层、手工设色
Acrylic, resin, stone-like painting, hand-colored
120×120×70 cm
5+1 AP
脊柱作为身体的一种隐喻,同时也常常被“背面”捕获,并常常成为阴性、黑暗、残酷的客体。弗里达的脊柱自画像、安格尔的脊柱侧弯大宫女,古斯塔夫·莫罗最甚,圣约翰断头的脊柱在好长一段时间成为我的童年阴影。后来,大学时期的解剖课上,我终于被希腊神话的另一个关于脊椎的故事治愈了。我了解到承托我们头颅的第一颈椎(脊椎)寰椎Atlas,其名字的来源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阿特拉斯。他负担着整个地球的重量,与寰椎承托着整个人的智慧中枢异曲同工。让人不禁感叹现代医疗的浪漫。(说句题外话,“文明6”游戏的封面就是Atlas)话说回来,脊椎在QQ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其实更多承载着一种美学的作用,一种有关支撑和维系的美。
《Virola》将这种支撑和隆起作为机体结构的合法性打破,原本作为桌子支撑的脊柱却在边缘的切线处逃逸,成为了一条百足虫。这让我联想起汉斯·贝尔默也在自己的一系列“身体装置”中确认了关节的主体性或者说一种主体间性。说白了,关节的意识有可能并不在骨骼,而在骨骼与骨骼间用以活动的缝隙。想到关节在某些情况下具备咔咔作响的恐怖潜能,我就觉得这件作品的木头材料阻止了它坠向噩梦的动能。《欲望崇拜》中,佛塔那响尾蛇尾般的轮廓和肉体触感,将“死亡”宣判为有机,也让仪式作为了人的意志和注目,充满了在场感。其质感上的液化处理让我自然联想到洞中融润的钟乳石,但锋利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壶耳和尖顶又一次戳破上一层语境,进而在夜间微光(荧光材料)的呼吸感中,如同米诺斯文明中的章鱼陶罐,生物机体和图腾灵光最终合二为一。

许嘉琪 / Xu Jiaqi
Virola
2024
北美胡桃木 / North American walnut
尺寸可变 / Variable size

汉斯·贝尔默, The Doll (Maquette for The Doll's Games), 1938

许嘉琪/ Xu Jiaqi
欲望崇拜/ Stupa of Desire Worship
2024
树脂/ Resin
H 52cm,φ 20 cm
5+1 AP
在QQ以往的作品中沁透着明显的“狮子”语言学问题:花儿很美,但美不能只用花来解释,美是没有绝对对照的客体(甚至椅子也没有其标准的客观范式),所以体验美就成了一种认识角度的实践,其中的象征根据我们自身的实践经历而流动。比如《Wings》中发展自身体语的言延伸,硅胶所模拟的肉体和肉体包裹下若隐若现的羽毛,我们便能很快联想到“未成年的天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天使的形象是“人+翅膀”,未成年则由稀疏绒毛和裸露肌肤组成。虽然我们并没有能力经验鸟的生活,但“天使”的替代性让我们能短暂抽离日常。但未丰的羽翼却又让我们害怕成为下一个伊卡洛斯。除了源于某种未成年的癔症外,《Wings》也在考量一种不可能的实践,如果身体的逐渐丰满意味着成熟的经验和作为人的在场。那么母体中尚未降生的婴儿,则指向一种尚未分化、无需秩序和经验便可自足的神话体验(先验甚至超验)。语言学中的“前语言时期”也就是婴儿尚未习得语言时的状态也经常与神话混同,肢体反应和本能仍然象征着混沌的可能,或许这也作为一种解释,为何当下的新锐艺术家更加想要描述一种“先验”的感知:更加接近一种“无痛”的脱经验的实践。

许嘉琪 / Xu Jiaqi
Wings
2025
硅胶、螺丝、高精度泡沫、镜面贴纸
Silicone, screws, high-precision foam, mirror stickers
40×110 cm * 尺寸可变,可穿戴装置 / Variable size, wearable device
3+1 AP
QQ的创作并未停留在解构与隐喻的游戏层面。就像某种症候和缺憾的积极作用力,她作品始终保有一种稚拙而灵性的温度,一种朝向“尚未被语言分割的世界”的乡愁。那或许是婴儿的前语言混沌,是伊卡洛斯还未坠落的那个瞬间,是神话仍与肢体记忆相连的原始场景。而我最近也反复地咀嚼了《美国精神病人》这部寓言体电影。好多人觉得这是一部大卫·林奇式精神分析片,我部分同意,我觉得它所指对象并不单单是个人或者群体,还有一个群体之上的结构。类比QQ最喜欢的动漫作品《JOJO的奇妙冒险》系列,一群不同症候的病人和非人,却藉由可见与不可见的力量,带着创伤和癔症,首先拿起工具、最终抵达丰饶。

左:电影《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2000)
右:动漫《JOJO的奇妙冒险》系列
文/高江波
艺术家 | Artist

许嘉琪 | Xu Jiaqi
1994年出生于杭州,2017年毕业于浙江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学士学位,日本武蔵野美术大学映像科研究生,2022年驻留于德国莱比锡PILOTENKUECHE。
她以装置、雕塑、绘画、录像等多种媒介进行创作,这些作品联系着神秘学、符号学、自然与考古等元素,并尝试探索和创造一种独特的隐喻式的能量场域。在使用不同材质的材料的矛盾感来表达自己独特的美学思维的同时,她相信美是唯一连接身体自由意志的本源。
近期个展:”许嘉琪个展“,PIN Gallery(北京,2024); ”元祖来电“,ABI Space(杭州,2023)。
群展经历:“剪刀、纺锤与纺线”,美成空间(深圳,2025);”Hyperhood附近分子“,马丁戈雅生意(杭州,2025); ”ART OnO艺博会“,CON_Gallery,SETEC展览中心(首尔,韩国,2025); ”AA+ALL STARS卡牌跨年项目“,AA+Plus,油罐艺术中心(上海,2025); ”Meme To Jam“ X sign Space(杭洲,2024); ”Veins of Dreams“, Artsect Gallery(伦敦,英国, 2024); ”SPLINTER CATALOG“, Untitled Gallery, CTM音乐节(柏林,德国,2024); ”合成生活:数字时代的影像艺术“,成都当代影像馆(成都,2023); ”蟹腿项链:跨年装置项目“,Loopy club(杭州,2023); ”曲登“,Playground(上海,2023);”亚细亚的迷子“,The 27 club (东京,日本,2023); “歌舞伎町纯爱战士2.0”,ALL club (上海,2023); “Archetype”,ALL club (上海,2023); Pleasure Seed, ARSAVANTl (莱比锡,德国,2022); ”Portal“, Forestlimit (东京,日本,2021)。
Jiaqi Xu, born in Hangzhou, China. Bachelor's degree in photography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Imaging at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Japan. She has been in residence at the PILOTENKUECHE in Leipzig, Germany in 2022, where she has been working in a variety of mediums such as installation, sculpture,painting, video, etc.
Her work connects with elements of the occult, semiotics, nature, and archaeology,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and create a unique metaphorical field of energy. While using the paradoxical sense of different materials to express her unique aesthetic thinking, she believes that beauty is the only source that connects the free will of the body.
Her recently solo exhibition include: “Xu Jiaqi”, Pin Gallery (Beijing, 2024); “Ancestors Call” ABl Space, (Hangzhou, 2023).
The group exhibition she participated in: “Scissors, Spindle and Thread”, Gallery MC (Shenzhen, 2025); “Hyperhood”, Martin Goya Business (Hangzhou, 2025); “ART OnO Art Fair”, CON_Gallery, SETEC Exhibition Center (Seoul, Korea, 2025); “AA+ALL STARS ”, AA+Plus, Tankshanghai (Shanghai, 2025); “Meme To Jam”, X sign Space (Hangzhou, 2024); “Veins of Dreams”, Artsectgallery (London, UK, 2024); “SPLINTER CATALOG”, Untitled Gallery, CTM Festival (Berlin,,Germany, 2024); “Synthetic Life: Video Art in the Digital Age”, Chengdu Contemporary Video Museum (Chengdu, 2023); “Spirit of Rave: A New Year's Installation Project”, Loopy club (Hangzhou, 2023); "mchod-rten", Playground (Shanghai, 2023); “Asia's Fanatic Son”, The 27 club (Tokyo, Japan, 2023); “Kabukicho Pure Love Warrior 2.0”, ALL club (Shanghai, 2023); “Archetype”, ALL club (Shanghai, 2023); “Pleasure Seed”, ARSAVANTl (Leipzig, Germany, 2022); “Portal”, Forestlimit (Tokyo, Japan, 2021).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