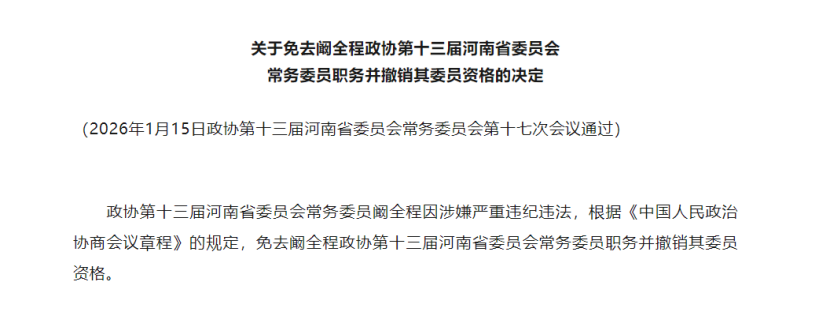周恬语:千惚之橘
展览时间
2025.12.13 – 2026.1.31
展览地点
今格空间|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1187号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2层
「周恬语:千惚之橘」今格深圳 展览现场
展览标题中“橘”的意象是如何确立的?你如何理解“千惚之橘”(It’s a natural cause)这一标题?
周恬语:橘其实就存在在我的作品内,一个类似橘子的橙色小球反复的出现在画中,以一个漂浮的姿态。而橘本身也出现在了我的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每天被我观测和看见的实体。在2024年我刚搬进我的工作室时,有一个窄长的、有窗沿的窗户,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放了一颗橘子在窗沿上。在工作室工作的一年时间里,橘子和我每天都在见面,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橘子,但是我的潜意识一直在看着它。而随着一年时间的变化,橘子的外表也在经历改变,它逐渐变得干瘪、变色,失去了原来的饱满,最后变成了深黑色,在我彻底搬离前,橘子被我丢了。随着时间过去,橘子不再是原来的橘子。橘子一直作为一个在我工作室漂浮的物体存在,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符号,在我的作品内存在。
千惚之橘的惚字,在汉典中的解释为“怳惚,微妙不測貌”。我的作品想要描述的正是处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不存在真实物理形态的物。同时,我在探索的内容是物的结局——在不同的作用力下,物终究会进入一个结局的状态。英文标题‘It's a natural cause’同时也是一副画的标题,画中的一部分描绘了橘子的四个不同生命阶段,标题暗示了橘子自然的消亡过程。

周恬语
《千惚之橘》
亚麻布油画
137 × 137 厘米
2025年
你曾将创作形容为一个“解码”(decoding)的过程。相较于绘画的最终成果,你似乎更关注创作过程本身。你的绘画过程通常包含哪些关键的判断与决策?
周恬语:我的绘画过程通常由直觉进入到逻辑的解析。我认为直觉能给我我本人所不知道的、关于我自己的信息,它会告诉我没有逻辑的、关于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通常包含由颜色和形状产生出的画面。我依靠直觉组建一幅画最初的构思。而当我开始绘画时,直觉和逻辑会在过程中反复地互相对话。在直觉做出自己的选择后,逻辑会反复追问做这个决策的原因。例如,某个颜色的反复使用很可能源于我自身对这个颜色本身强烈的私人记忆,或者是我对这个颜色特质的主观理解。绿色在我的主观感受里的特质和湿度有关,不同的绿色可能代表着干燥的或是湿润的。而绿色本身对我来说是难以捉摸的、深邃的,就像是抚摸一个不平整表面的感受。
逻辑的作用是探索直觉的想法从何处来,探索绘画的原因和目的,以及如何更深度地挖掘自我。而经过反复的自我解答,自我探寻,自我提问,我才会得到一个更加确信的答案。所以我认为我的绘画一直是自私的行为,为自我服务,通常解决的也是我自己的问题。结局只是过程的一种定格和过程的存在证据。我在意创作过程大过于创作结果。
你提到创作往往从“直觉”开始,能否进一步谈谈这种直觉通常从何而来?在“由直觉进入到逻辑的解析”之后,你通常是如何具体地进入绘画行动的?
周恬语:我无意识地捕捉周围的形状:地铁站脱落的墙皮,光秃秃的盆栽,一直看到的、反复出现的一个颜色,一直在循环的一段空间。因此我会控制我身边出现的事物,我日常使用的物品都会先经过一些颜色上的筛选,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穿的一件毛衣的颜色反复出现在我的作品内。直觉使我从无意识收集到的图片内寻找最符合的信息,而在对待来源不明的事物时,我时常保持警惕,我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去看到一些信息。
直觉帮我记住我以为自己记不住的,直觉使我忘不掉也逃避不了。时常有人评价我的画给他们一种nostalgia的感觉。记忆不是最准确的,它包容了自我扭曲。我把自己想要记住的作为记忆的主体,我看到我自己在记忆内,空间的颜色随着我的自我产生变化。直觉是我记不住的自我。
通常在开始创作前,我会问自己一些问题,或者给自己一个确定的主题,而后利用直觉快速解答。我会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在脑内构思画面,并且确定我要绘画的内容。逻辑会在准备开始实际的绘画、以及在创作之中时运作——我要确保自己在画每一笔时知道自己这么画的原因,而不是完全依赖直觉。在绘画时,我的动作必须是纯粹的,逻辑反复地确认我的行动目的,并且保持目的统一。绘画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它成为了纯粹的一个动作,不带有任何不纯粹的目的性。
你的创作既涉及个体经验,也不断与不同文化语境发生关联。个人身份与跨文化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创作思考?
周恬语:我的作品都关乎于我自己,我的创作目的也是我自己,我的画一直是自私的。
语言塑造了人的认知边界。在我的成长时期,我接触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这对保持我的自我有很大帮助,促使了我对自我进行思考。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绘画。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下,“好”有很多含义,我只能去思索自己的语言。
我一直在搬家,所以我习惯性地确保自己身边的东西都是易于携带和可以被搬走的。我也好像一直在回家,中学时每年平均四次往返两国;我也好像一直在离开,和我有共同经历的人也都逐渐离开了我往返十年的地方。十年之后,我存在在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漂浮着。
我思考着家的定义是什么,我又到底归属于哪里。
圆形在你的绘画中反复出现,既作为画面的“框架”(frame),也作为构成画面的形状元素。你是如何使用并理解圆形这一形式的?
周恬语:在架上绘画中,一个方形的框是一个默认的设定。框的外形迫使我去解决了一个我在绘画内遇到的问题:框的线条就像是在暗示一个四方的空间,就像是从窗户往外看,或是看向一个四方的房间内部。在抽象绘画的语境下,原本抽象的表达会被影响,抽象意义的图案被异化成了具象意义的心灵的风景或者空间。对此我寻找到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在画内自己定义框的形状。
在各个形状中,圆形成为了装载我的绘画内容的最优解。圆形只有一条边(或者也可以说是无数条边),可以简单地包裹、统一一切,把我画中的内容从空间中的无数物体变成一个物体。圆形让画面的内容被我想要的方式装载了起来,同时强调了画和现实的不同,带出了一个被我个人主观化的视点。
圆可以包容和承载一切,同时又会困住被包裹的一切。逐渐地,圆本身变成了我的画的内容里反复出现的符号:圆既可以被理解为生物,也可以被理解为死物,可以是橘子,可以是某个动物,可以是桌子的表面,可以是一个容器的横切面,是从井底往上看的风景,是望远镜内看到的画面。当圆可以成为和包裹一切时,观者不再清楚到底被圆困住的是不是自己,观者也不再察觉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观看着一切,是抬头还是低头。
周恬语
《倍数》
亚麻布油画
137 × 165 厘米
2025年
除了圆形,你的绘画中也会出现其他形状,它们往往以明亮的色块形式置于相对低饱和的背景之上,呈现出偏向平面、二维的画面效果。你如何在作品中处理空间感与平面性的关系?
周恬语:我的绘画始终呈现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所以我倾向将空间的维度变得不确定,让空间中存在不同的物体堆叠。背景的低饱和强调的是画中内容集体表达出的一种氛围,是不存在的一团空气,使得画中的内容物在重力上的表达飘忽不定。
我暗示三维空间的一些线索:物体的影子、在静物上类似阴影的颜色。在几副作品内,简单的三条线构成了空间的一个角落,一个目的是为了暗示画面中的角色处在室内的空间,在较为开放自由的背景氛围内暗示自由的局限性;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用最二维甚至是一维的语言涵盖三维的信息,将画面推向维度的中间。二维空间偏平面化的表达则更倾向于一种自我形成的符号,比如画中经常出现的三条线,是好像发生过、好似是静止的、不知内容为何的对话。无处不在的橙色球体也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我将三维空间和二维空间放在同一个画面内,来探索不同维度的空间组合在一起产生出的矛盾。我画的内容旨在创造矛盾,将画面放置在矛盾之间的灰色区域。
同时,一些图形在不同的画中反复的出现、复制,产生了不同的体系,甚至脱离了原本的含义。在不停的复制下,原本具象的内容减弱信息,并成为更抽象的符号,而抽象符号又根据不同的画面衍生出不同的含义。经于我人为的复制而不是机械式的重复,反复地扩大了原本在相同符号中细微的不同,最开始的同一形状的本质和多次复制后的形状会产生新的矛盾以及冲突。我逐渐通过反复描绘同样的形状来创造新的讯息和语言。
周恬语
《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
亚麻布油画
160 × 90 厘米
2025年
背景始终是你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画布的原始质感被有意保留下来,形成一种接近“原始”(raw)的状态。你为什么选择这样处理背景?它与画面主体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周恬语:在学生时期,本科的前半段,很多时候我都会用已经准备好的画布——白色的、有一点刺眼的、好像真实世界里不会出现的背景颜色。从那时起,我的绘画语言就一直在探讨完成和没有被完成的画面。对我来说,没有完成的画面也可以是一种完成,我刻意不把画画得完整,不把背景填满。白色的背景太过强烈和刺眼,我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真正地看清我在画的是什么。我开始尝试在亚麻布和棉布上用透明的基底来画。尚未被画过的画布更加传达出未完成的、还有潜力的空间,以及已经被放弃的、刻意不被触碰的部分。亚麻的质地会更容易吸收和抓住颜料,棉布上了油画颜料后也会更加的厚重。我在绘画时通常喜欢用一笔画更多的部分。为了延长一笔的动作,我会用比较多的松节油来稀释颜料。亚麻画布会很好地吸收油比较多的颜料,所以我的一笔才可以在画布上画得更久——虽然在颜料快没了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用干枯的笔刷继续画下去。在开始绘画时,背景的颜色也会影响画面整体的氛围。亚麻原本的色调就很接近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它是可以呼吸的,而呼出的空气是偏固体的、稍微有点凝重的。
周恬语
《休息吧》
亚麻布油画
120 × 70 厘米
2025年
你提到过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是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去描绘一个主观的事物或者场景”,在你的创作中,这种“客观性”是如何被建立的?你又如何在这一视角下将个人经验与主观感受嵌入画面之中?
周恬语:客观性和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掩饰和工具。当观看自己的记忆时,人类通常使用第三人称。
一个原因是,我在绘画内和我自己对话,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对话,客观性和主观性对话;第二个原因是,我不愿意把自己直接地暴露在画布中,所以我假装自己是看着自己的第三人称,用第三人称来描绘我本人。我想站得离我自己很远,我想冷静地描绘我自己。
第三人称可以描绘的内容也会更多一些。在一些画面中,我想要描绘的是一个群像。在这个视角下,我把我的主观假装成普世的客观。空气、空间、时间变得更加可视,我自身的感受可以被自己触摸,我可以和自己开展对话,上演一出舞台剧。
对你而言,绘画像是一场自我对话。在你看来,创作者、画中人物与观者之间,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
周恬语:画中的生物是没有独立意识的,他们共用同一个意识。画中的角色都可以是我自己,或者是我记忆中的某个人。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认为我的绘画是自私的,是不为观者服务的。为了不让观者理解我,我甚至创造出各种矛盾和谜题。我既是创作者也是观者本身,我扮演所有的角色。
通过陷阱、谜题,和一点点希望,可以让观者真正地思考画中的内容——矛盾的,令人困惑的,好似能看懂,好似能抓住一部分物体、转瞬即逝的线索和灵感。每一个观者都会问我绘画中的内容具体是什么——是不是一份水果?是不是一种动物?我通常都会说我不愿透露,或者告诉他们答案,让他们恍然大悟,以为自己明白了。绘画的表面、绘画的实际物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的内容是什么。莫兰迪在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启发。他永远在画容器,但是没人知道容器内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感受到,他画的好似是容器,但并不真的是容器。绘画的语言,一直是一种在文字被发明前,就能传达出用文字不能具象表达的抽象内容的语言,在牙牙学语时,人类先学会了绘画。在矛盾和谜题之下,我探讨的真正内容没有办法被具体的语言所描述。
你在创作中反复提及“结局”这一概念。在你看来,本次展览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阶段性的“结局”?在这一节点之后,你如何看待自身创作的延续与可能展开的方向?
周恬语:结局作为我这次探讨的主要主题,对我来说是没有结尾的。展览中的一部分作品是对结局之后的描述,而结局本身就是一个违背逻辑的一个概念,没有真正的结局存在——时间一直在在三维世界中流动、前进,结局永远在被翻新。我认为,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我的作品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有所改变,但是一直以来,我思考的,我画下的,我探讨的内容,一直在我的绘画语言中不断延续。以前的内容没有真正结束,而是一直沿着结局之后的路线行走。在我的绘画语言中,内容也是随着时间往前流动的,过去的内容就像记忆一样被永远留存,而将来的内容也没办法脱离记忆运行。微小不同点产生的特殊性,以及尴尬的、或是没有被发现的日常奇观,是我的绘画一直在探讨的内容。结局属于是这个探讨点的一个分支。“结局”这个主题还是会一直附身在以后的作品内,但在这个阶段之后,内容的主角的确会随着时间转换成另外的内容。
关于我接下来的创作,在画面上,背景的水墨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创作了一个更加游离、具有共鸣,以及难以被触摸的氛围,我会在下一个阶段尝试解构这个背景给我和整个画面带来的影响。而在内容上,我还是会探讨尴尬的微小不同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和我自己在现有人生阶段所面临的变化产生关联。
这次展览中的主题结局是什么?
周恬语:我想要探讨的并不是结局本身的悲观,或者是面对结局时的恐惧。结局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对一个时间段,一个事件,客观的命名。在时间的线性流动中,结局是一个没办法被停止的存在,没办法被预测的未来。我意识到人类在有意识地回避结局。主观视角下结局或被逃避,轻拿轻放,被刻意忽视。而在客观视角下结局好似没有发生过,在一瞬间的停顿后不会留下太明显的痕迹。当我意识到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偏差和矛盾之后,我的思考出现了裂缝。
在经历了一个熟悉的人的死亡之后,我才清晰意识到了这个偏差的存在。因为我和他不常见面,在我得知他的死亡之前我不曾真正地认识到他的结局已经到来,我也没办法客观地理解到生与死的区别,就像是薛定谔的猫。当我得知他的死亡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了他的死亡。
主观上的信息发生了改变,结局才真正地开始转圈。那在我主观的了解到此结局之前,这个结局就没有发生了吗?
结局不是一个句号,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不是事情发生的一瞬间,而是每一次主观意识到的每一段时间,是重复的提醒。我感受不到他的死亡,却真切地理解了他的死亡。
红色的雨一直包裹着他的结局,雨滴很细,几乎看不到是雨点。时间是在一直循环的一大段。
采访 / 撰文:李芊千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