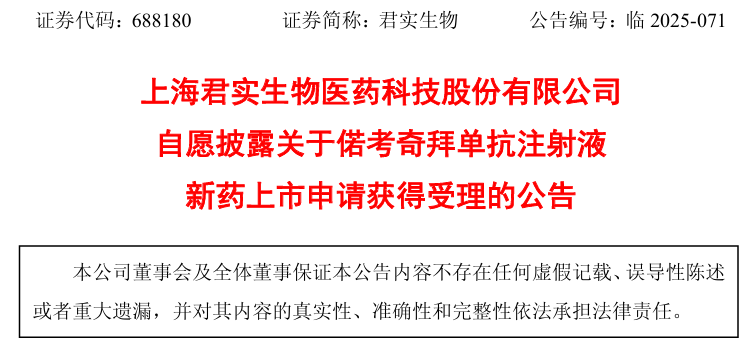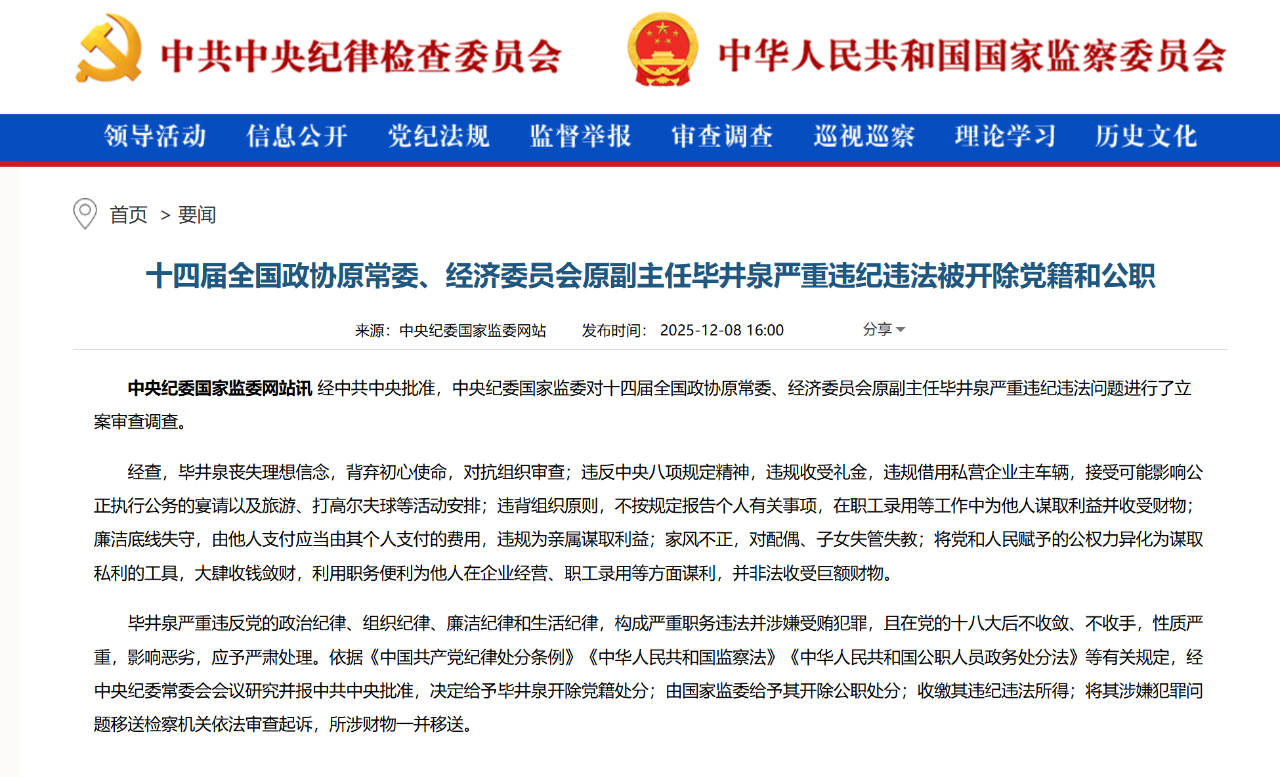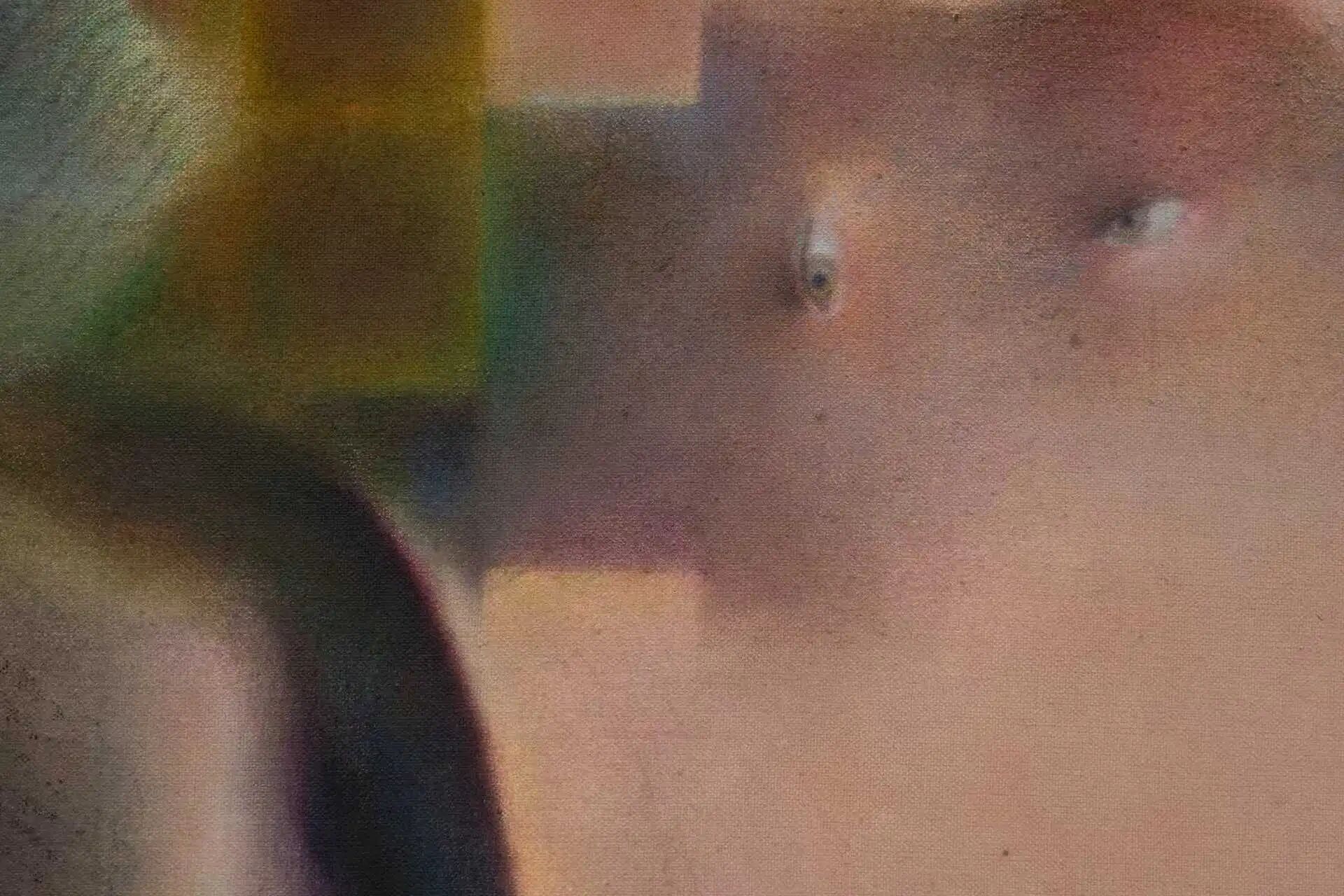余友涵1980年笔下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1957年,余友涵初学绘画时,他曾经来到这里参观“苏联八位著名美术家作品展览”,并在现场写生了雕像“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
对谈嘉宾:
余宇(余友涵之子、Art On Time创始人)
黄勖夫(收藏家、X美术馆创始人、策展人)
赵剑英(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
于瀛(艺术家、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ART021 FORUM
时间:2025年11月14日

论坛文字实录
赵剑英: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我们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的举办的这个论坛。我是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赵剑英。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参加座谈的嘉宾。坐在我旁边的余宇,他是余友涵先生之子,也是art on time的创始人,他对余友涵先生艺术遗产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梳理;然后是我的好朋友勖夫,他是x美术馆的创始人,也是活跃于国内和国际的艺术收藏家、策展人和重要的推手。我和我们应空间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艺术家于瀛老师,是我们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关于“余友涵研究”一系列展览和出版计划的参与者。我想这不只是我们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的新书发布,更主要是一次关于探讨和介绍“余友涵研究”未来规划和愿景的座谈会。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这几位来到这里。
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一直致力于对艺术史研究的推动,我们对清华大学、深圳美术馆等等学术机构,以及独立的艺术史学者进行了赞助和支持。“余友涵研究”是我们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研究计划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起点,因为余友涵先生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自己的创作,而且是出于艺术史的前后关系和脉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
展览海报,深圳美术馆,2025
今年年初,我们在深圳美术馆举办了展览“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这个展览项目是我们委任刘鼎、卢迎华两位优秀的艺术史家进行的研究项目的成果展,实际上在展览之前,两位学者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数载的时间,尤其是进入展览筹备阶段,我们和研究者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和沟通,虽然两位专家不在现场,我在此要感谢两位付出的心力与时间,我们支持的这个研究专著即将于年底之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这是这本书的样书,里面包含两位学者的六个篇章的长篇论文,对应着展览的不同章节。深圳美术馆的这个项目,获得了大湾区的市民和观众的积极反馈,在展览期间有200多万人到访参观,并且成为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
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在展览筹备的过程中,我们计划制作一部关于余友涵老师的纪录片,目前这部纪录电影正在进行后期的制作、剪辑和补拍。以此为契机,在余宇先生、沈峻老师的支持下,拜访了余友涵一生中不同时段的交往密切的亲朋好友,和这些前辈、同道的交谈中,好像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个不同的余友涵先生人生和艺术的侧面——余友涵先生作为老师、同事、邻居、朋友、前辈、上海人、艺术家、父亲、研究对象……各种各样身份中的他。他们的回忆总是带着幽默或者沉痛的细节,让我能够体察到余友涵先生不同阶段创作发生时的生命状态。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些谈话如此重要,远远超出了一部纪录片所能容纳的信息量,因此我们将所有的对话整理成文字,编辑了《长乐未央:同时代人记忆中的余友涵》这本书,目前我手上这本,是这个系列对话集的第一册,未来我们想要访问更多的人,完善这本书的后续。
余友涵纪录片中访谈部分拍摄现场
(上图:薄小波;下图:卢迎华、刘鼎)
今天这个论坛,是以两部出版物为契机开展的,我们以目前已经出版的书籍为基础,试图为一项长期的学术工作——“余友涵研究”,勾勒其外在的轮廓与内在的思想方法。余友涵先生的离去已逾两载,但在艺术史的长河中,我们对他的认知,或许正如我们今天论坛的标题“长乐未央”所暗示的,远未抵达终点,而是处于一个漫长而充满可能性的开端。“未央”,既是未尽,也是未明,它指向一种持续的、未完成的状态。这也正是我们启动“余友涵研究”这项长期学术计划的初衷。今天的对谈,我们希望从机构实践、艺术研究、情感档案与收藏策展等多重透镜出发,不仅讨论我们已经看到的“阶段性成果”,更试图探讨“余友涵研究”在全球艺术格局与本土语境下的目标与愿景。它不应仅仅是对一位重要艺术家的盖棺定论,更应成为一种方法,一个视角,用以观察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复杂时代。
《长乐未央:同时代人记忆中的余友涵》(第一辑)
赵剑英主编,书艺出版社,2025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
卢迎华、刘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本次论坛要感谢021的支持,和021的三次合作都是在发布我们的研究专著,从我们研究余友涵、丁乙、冯良鸿师生三人的《长乐路的风》,我和许知远的《何多苓:游戏之必要》,研究徐累、邵帆、刘丹的《极地清晨》,到这一次,我们感到021团队不仅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艺术博览会团队,他们不仅对于艺术市场专业、也愿意长足地分享和推动学术,这和我们的愿景非常一致。因此我们在D06展位,也带来了一个研究项目的序篇,也欢迎大家来我们展位看展。
“混沌考:风景的发现”展览现场,ART021 SHANGHAI,上海展览中心,2025

议题1:档案
赵剑英:
余宇老师对我们的研究计划、展览、出版等等,给予了非常关键的支持。余宇自幼随其父余友涵辗转于画室、写生现场与展览空间,一起旅行、一起听音乐、一起摄影,他亲历了余友涵从开始探索艺术到蜚声国际的全过程。在访谈中,余宇回忆了他的父亲余友涵先生作为艺术家、教师、父亲的多重角色。余宇近来整理挖掘和梳理了很多余友涵老师早期的档案,包含笔记、日记、草图、书信等等,这些梳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新的视野和感觉,在刘鼎、卢迎华、谈晟广三位老师的研究中已经首先运用了这些材料。
另外,您之前也编过一本《画中有话》,这本书把余友涵老师的一些只言片语和作品的局部结合在一起,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很能想象出您在整理文献的状态,在作品中发现局部,在文章里发现段落,好像这本书呈现了你在梳理过程中那些灵光一闪的瞬间。余老师您能谈谈您在梳理余友涵档案过程中的感受吗?通过这些档案,您对您父亲有什么新的理解? 有没有哪个发现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余宇:
我之前也参加过一些对谈活动,但是几乎每次都是以晚辈的身份参加,今天忽然意识到,在座几位都是国内最重要的艺术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年龄都比我小,我想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艺术史是要传承下去的,艺术研究的工作也在一直朝着非常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剑英问到了关于编书的一个问题,我也带来了手上这本《画中有话》。我本身是一名建筑师,其实并没有直接延续我父亲的艺术创作工作,直到2017年,父亲身体出现一些状况后,我才以助理的方式参与他的工作,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由于我不是艺术科班出身,在整理过程中,其实更多是透过这些文献去学习、去理解他。另外,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对平面设计也很有兴趣,对编书这件事情有我自己的偏好。
说起来也非常遗憾,从2017年我开始做相关工作的时候,父亲的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下降了,所以我后来对于父亲大部分的学术方面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他留下的文字和作品去学习的。在我整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父亲很多话都非常有意思、有价值。有些观点我非常认同,或者说,我能感觉到他是在探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2019年我开始编这本书时,其实开始艺术工作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当时定义自己为一个初学者。当时有些话我其实不太理解,比如他说“当代艺术起源于文化,而非起源于生活”,当时有点儿不明觉厉,不太清楚这句话的一个准确的意味。直到几年后的今天,我才逐渐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理解这句话——我想,文化或许是更多人的共同经验,是一群人集体体验的沉淀。
我想我当时编这本书的时候,并不是把这些话当作《圣经》一样的真理,而是觉得父亲关于艺术、关于人生的这些思考,值得被更多人看到。我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文字和插图去认识他,理解他思考艺术的方式。无论是艺术工作者还是爱好者,我们其实都需要面对和思考这些基本问题。
在整理中,我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父亲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朋友,他始终在给予周围人引导和帮助。我想这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我父亲出生在1940年代,建国初期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他曾经回忆,上小学时午饭没地方吃,学校了解情况后,就让他到教师食堂和老师们一起用餐。他一直对这个事情很感念,而且记忆犹新,这件事他直到2010年写《自问自答录》时,还专门拿出来讲,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有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是他和邻居范先生一家的交往。我爷爷奶奶并没有艺术方面的背景,而邻居范先生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而且是一位很优秀的艺术家,范师母则是一位音乐家。父亲小时候常常待在范先生家里,看他的画,翻阅他大量的艺术藏书,还可以听范师母弹琴。他有时听着音乐就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时琴声依旧。每次读到这样的段落,都会觉得特别感动——正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无私的关爱,为他创造了很好的艺术启蒙环境,也最终引领他走上了艺术之路;同时,也造就了我父亲这样的人格,我相信,我父亲正是以他细腻的感知,把这份来自他人的温暖,在后来的岁月里,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赵剑英:
谢谢余宇。你让我们看到了艺术背后那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以及那些日常细节如何最终升华为艺术的精神内核。这确实为我们理解余友涵先生的作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维度。你的视角和一般研究者不同,不仅仅是找寻艺术风格生成的逻辑链条,更是进行一场情感的考古。《长乐未央》这部纪录片因篇幅有限,未能将所有内容囊括其中,但受访者的表达非常充分、生动。在制片过程中,我们深感这部分情感档案同样珍贵,因此将其编辑成书。您在参与拍摄时,是否听到了一些过去未曾了解的、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长乐未央》纪录片拍摄现场,龚彦馆长与赵剑英
余宇: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宋涛老师,他曾经是我父亲在工艺美校时的学生。那是90年代后期,我父亲刚从美国回来不久,退休之前那几年,可以说那是他艺术与教学思想都非常成熟的阶段。当时的宋涛还是个十六七岁的中专生,因为和我父亲关系比较好,他们课后常常一起在校园里散步。从他那里,我听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让我感到,老师的一句话有时候真的能深深影响一个学生的方向。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余友涵90年代在上海工艺美校授课
我父亲在上海工艺美校长期教基础课。有一次上色彩课,有学生请他帮忙改画。一个女生递过来一个刚洗干净的调色盘,上面新挤了颜料,但我父亲却说:“我不要这个。”然后他拿起了宋涛的调色盘,宋涛的调色盘是很久没有洗的,所有的颜色都混在一起。他说:“我喜欢这个。”后来宋涛告诉我,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理解了绘画中灰调子的重要性,以及纯色如何使用才恰当。
还有一次,有学生问他:“余老师,怎么才能在画面上画出三维的体积感?”我父亲反问:“画布是平面的,你为什么非要把体积感画出来?”当时那个学生有点懵,甚至觉得老师是不是在否定他。但其实,这恰恰反映出我父亲对绘画本质的理解。他认为绘画的核心特质就是平面性,它和雕塑不一样;用平面去模拟立体,只是绘画中的一种手法,而不是绘画的全部。
类似的问题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老是画不像?”我父亲的回答是:“你不必追求画得像,但要画出你心里的感觉。”对中专阶段的学生来说,这些话当时未必都能听懂,但我相信,有心的学生日后回想起来,一定会受益匪浅。我的父亲和学生们相处也总是很幽默,计文于老师这次访谈提到,我父亲给学生讲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历史,有位调皮的学生很潦草的交了份作业,说自己是“极简主义”,我父亲说:“对,你这是极简主义,我给你的分数也会是极简的。”工艺美校虽然是一所中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培养出了大量上海当代艺术家——我想这和那里的教师与教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可能不少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中国最早使用丙烯颜料的艺术家之一,他从1980年就开始用丙烯创作。我以前的理解是,一方面工艺美校接触丙烯比较早;另一方面上海有马利颜料厂,条件便利;而且丙烯可塑性强,画厚像油画,画薄如水墨,干得快、使用方便。
但赵川老师,他是我父亲多年的好友,在访谈时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他说,当时丙烯颜料历史不长,没有太多传统经验的包袱;我父亲正是看中这一点,认为可以在这种媒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经验。他是从“另辟蹊径”这个角度去大量使用丙烯的。其实我父亲也常去研究大师的作品,但他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的经验,并不是为了变得和他们一样,而是找到自己的方法。我想,这或许正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都应该具备的自觉。
赵川在《长乐未央》纪录片拍摄现场
赵剑英:
从档案整理、艺术分期到理论与历史化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档案的角度出发,您希望这些资料未来以什么样的形式面向研究者和公众开放?
余宇:
我们的确有不少想法和计划,但仅凭我个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需要与学术机构携手推进。在此,我想分享一个初步的设想。
首先,我觉得这些艺术相关的文献是应该跟作品的档案放在一起。艺术史的研究不应是“文本主义”的——不能只从文字到文字的研究,而是从作品出发到文字的分析。作品的图像本身就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始终要与作品紧密结合。
其次,如今国内越来越多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都已意识到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这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合作空间。我相信在线下会有类似于档案馆这样的分门别类的资料,我希望未来能建立起一个实体与线上相结合的档案系统。线下设置分类清晰的资料空间,方便研究者查阅;同时,也考虑到许多朋友需要远程访问,因此必须建设便捷的线上平台。
最后,我也在关注AI技术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已尝试着搭建个人知识库,并探索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信息处理。尽管这项技术目前尚不成熟,还不能直接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来使用,但我相信它未来可期。因此,我也期待能将传统的档案保存方式与新兴技术有机结合,为艺术文献的整理与传播探索更多可能性。
赵剑英:
谢谢余宇。的确,在AI时代,严肃和准确的研究、详实的档案整理和分享,必须值得重视和格外的小心——那也是下一轮人工智能学习和引用的原始素材。

议题2:视角
赵剑英:
我还记得我和上海PSA的龚彦馆长聊余友涵时,她曾经说过,对一个去世的艺术家最好的纪念就是不断地重新展览和讨论他,不断地提及和想象他,这样他的艺术就是永恒的。同时他也提到,余友涵研究的核心,在于如何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框架。这也是高名潞老师、赵川老师、栗宪庭老师共同的关切。比如他的“圆”系列被西方策展人纳入抽象主义谱系,但其内在的“道”的哲学又使其区别于比如赛-通布利或者罗斯科等西方抽象艺术;他的政治波普被贴上“中国符号”的标签,但实则是对全球化视觉暴力的迂回批判。在90年代,余友涵在美国写给薄小波的信中,提到了“来到纽约是为了告别纽约”。
X美术馆今年做了一个关于抽象艺术的展览“抽象的收藏303”,而且是你亲自策展的。在我记忆中,这也是X美术馆第一次用“抽象”作为题目来做的展览。海报上也选用了余友涵老师的作品,勖夫,你作为收藏家、策展人和美术馆的创始人,众所周知,你的艺术视野非常宽广。你从什么时间开始关注、并且收藏中国本土发生的抽象艺术实践?进一部分的,你如何看待余友涵创作的价值?他的作品哪些方面的独特性最打动你?在你决定收藏时,你有没有受到学术研究的影响?
“抽象的收藏303”展览海报,X美术馆,北京,2025
黄勖夫:
X美术馆的内容创作始终以馆藏为核心,我们的许多展览都是基于收藏脉络展开的。今年我们选择“抽象”作为主题,也是呼应近年来全球艺术界对抽象艺术的再度关注。艺术史的发展有时与时尚类似,存在某种轮回。在具象之后,抽象又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
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持续调研并学习了许多国内外艺术家的实践。大家可能了解,X美术馆主要致力于收藏和发掘青年艺术家,过去的馆藏展中,90%以上的作品都来自新生代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创作者。今年我们推出的“抽象的收藏303”展览,恰与另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项目:“抽象重造:20位四十岁以下的艺术家”形成呼应。这个项目是我们与法国第戎Le Consortium当代艺术中心合作推出的,其中也包括几位中国艺术家,例如近期在市场上颇受瞩目的李黑地,以及持续受到关注的张子飘等年轻一代。此外,也有像杰德(Jadé Fadojutimi)、露西·布尔(Lucy Bull)等国际上新涌现的抽象艺术家。
在策划馆藏展时,我希望能对这样的艺术语境作出回应。如果大家来看过我们的展览,可能会注意到,年轻艺术家往往更注重色彩的运用与视觉冲击力。但在我看来,抽象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个人审美与自身美学体系的凝结与总结。因此,在我们的收藏中,也纳入了部分早期艺术大师或已故作家的作品。这次展览的策划,正是希望促成不同代际艺术家之间的对话。
“抽象的收藏303”展览现场,X美术馆,北京,2025
在中国讨论抽象艺术,余友涵老师是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在此我也想感谢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说实话,我回国做美术馆的时间并不长,还在不断学习中国艺术史与其中的关键艺术家。我第一次见到余老师的原作,就是在应空间的北京空间,你们所做的研究及艺术史梳理,为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余老师承前启后的位置非常特殊:他不仅为艺术史作出了实质贡献,他的学生如今也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至今,我们关注余老师的作品已有两三年了,深感其艺术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也一直希望他能更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因此,在推进国际项目时,我们积极将中国艺术家向外推介。例如,当外国策展人来馆参观我们楼下的展览时,我们也会引导他们关注像余老师这样的中国大师。最近,我们还邀请了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基金会的负责人前来观看,就是希望为余老师争取更广阔的国际平台。就像刚才余宇谈到的,如今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或许越来越年轻,但我们的视野正越来越国际化。我也希望,在我们这一代的努力下,能够真正助力中国文化的“走出去”。
赵剑英:
今年三月份,作为我们委任卢迎华老师漫长的五年研究项目成果,我们在深圳美术馆呈现了“友涵与余友涵”这个带有回顾性质的展览。你当时作为我们的贵宾,出席了展览的开幕,你还记得当时在展厅中看到余友涵先生一生的重要作品,有什么感受吗?从作为观众的角度,当时展览中呈现的余友涵的艺术笔记、文献、草图和同时期的艺术界的背景资料,这些研究材料对你理解余友涵的作品和这个展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
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你曾经在美国学习艺术史,对抽象艺术的历史非常熟悉;同时你也有长期和深入的西方艺术界经验。中国抽象艺术的发生,首先得益于跨域东西的学术互动,在这个过程里保持着自己传统的艺术理念,从而呈现了出独特的面貌。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向世界,特别是向更年轻的、可能不熟悉中国特定艺术史语境和社会思想语境的观众,来呈现和阐释余友涵的艺术?需要研究者、学界、艺术机构为这些跨越疆界的对话,做哪些学术上的准备?
黄勖夫:
首先我认为,视觉艺术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有一个很珍贵的特质——它能够直接用视觉本身进行对话。尽管存在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但一幅绘画作为视觉作品,本身并不依赖语言的解释。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艺术家需要将自身的视觉语言和审美体系融入作品之中,这既是他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表达。当然,很多艺术家也会研究艺术史、不断学习,但这并非为了模仿,而是将所学与自身的人生阅历融合,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表达体系。
就像余老师所做的——他将生活中影响他的种种元素,无论是印象派的色彩、西方的透视方法、中国水墨的意境、风景画的表达,还是对“道”的哲学体悟,都自然而然地融入自己的创作。这种融合形成了一套完整而自洽的表达。而这样的表达,能够让视觉本身超越语言:即便不带任何解说,一位外国策展人站在他的画作前,无需了解背景,也能被深深打动——我认为这是艺术最可贵的力量。
当然,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一直以来所做的展览,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艺术家的人生与创作脉络。它让我们看到艺术家的每一段经历是如何转化为作品的一部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更好地了解到一位艺术家的每一段经历,他又是怎么把这些经历融入到他的作品里面的。深圳美术馆的“友涵与余友涵”作为一场回顾展,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它不是简单的把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作品陈列出来,而是通过文献梳理与创作脉络的呈现,还原出艺术家风格的演变过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展览不仅面貌很完整,对中国艺术史的整理与书写也有着很重要的帮助,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长乐路的风”展览现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21
“识觉之途”展览现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24
赵剑英:
谢谢勖夫的分享。作为X美术馆的理事,我在现场看了“抽象的收藏303”这场展览,我非常为这场展览感到骄傲,它不仅仅回应了新的艺术动向,也深邃地回应了艺术的既有历史。我想这值得成为一个标杆性的工作,希望新一代更多的美术馆和收藏家也加入传承、接力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来。

议题之三:框架
赵剑英:
《长乐未央》这本书除了余宇老师的大力支持之外,也得到了丁乙、高名潞、薄小波、龚彦、王薇、栗宪庭、计文宇、赵川、宋涛、谈晟广、卢迎华、刘鼎等诸位老师的支持。这本书最长的一篇,是我和于瀛老师的对谈,谈到了“余友涵研究”的一些前前后后。我想问于瀛老师,可以谈谈我们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对于余友涵研究的历程和感想吗?对于余友涵研究的框架,我们有着怎样的计划?
于瀛:
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对余友涵的研究,是从“长乐路的风”展览开始的,展题用“长乐路”这个名字,是因为余老师最早的工作室就是位于长乐路,当时余老师的学生们时常聚集在这个工作室讨论,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空间节点,但由于余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那个时期的交往,它已经深深嵌入了上海这座城市当代艺术起源阶段错综复杂的肌理之中。我们新出版的这本《长乐未央》,延续了这个意思。“未央” ,暗示着余友涵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不意味着他艺术生命与思想效用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标志着其作品从“创作”的现场,转向“阐释”与“问题化”的广阔领域,进入了一种“永未终结”的状态。
余友涵在长乐路的工作室
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一直有一个愿望也好,学术抱负也好,是想要把中国20世纪、21世纪的艺术史重新进行梳理。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部被各种“断裂”叙事所切割的艺术史图景:1920年代的“启蒙”与“决裂”,1940年代的“救亡”与“转型”,1980年代的“新潮”与“反思”,1990年代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这些被高度标签化的历史单元,塑造出了一种种顽固的认知模式。在这个前提之下,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似乎都仅仅是为了完成其所属时代的“历史任务”,而后便被迅速翻页,谈不上经验的连贯性,或是情感的连贯性,下一个世代又要“重新学习”——其中错综复杂的缠绕、延宕、回返与潜流在这个过程里被无情地抹除了。
“「作为作者」策展研究项目”展览现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25
余友涵先生生于40年代,他经过以上说的这些“断裂”的过程,他的工作虽然面貌多元,但他的思想底色并不呈现为“断裂”。应空间长期以来所崇尚的历史化的工作,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封存,而是不断激活思想资源以介入当代知识构造的实践。因此,我们的“余友涵研究”,是要把余友涵先生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里面,形成前后上下的对应关系,把他作为原点和坐标,作为一个可以不断折射不同历史光线、测量各种思想张力的棱镜与尺规,并且从他出发探究更多的艺术家和艺术现象。正如龚彦馆长之前所说,“我们纪念一个艺术家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谈论他”,我想,“谈论”的目标是让他的实践和他的艺术思想重新问题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学者来参与,在跟不同的学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到余宇整理的这些档案。档案不是中性和静止的史料堆积,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思想场域,当我们邀请众多学者进入这一场域时,每一位研究者都携带着其自身独特的知识谱系与问题意识,找到不同的兴趣所在。当然,我们很愿意支持、鼓励和激发这种持续的、多元的叩问。这些深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研究视角,也帮助我们扩充对余友涵研究的范畴。我们也愈发感觉到,在余友涵先生身上,总是能很精准的切中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进程里的很多关键性的问题。
《长乐路的风》研究专著,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2023
比如,余友涵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开始临习石鼓文。在各种书体中,他偏爱石鼓文,绝非单纯的书法练习或复古趣味——我们必须将这一行为置于清末以降巨大的文化转型脉络中加以审视。石鼓文,作为上古文字的遗存,在晚清碑学运动的浪潮中被重新激活。以傅山等为代表的学者,倡扬碑学的雄强、朴拙与刚劲,其意图远超出艺术风格的嬗变,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政治行动。他们试图以此“扫除过去国家积弱的文气”,用一种源自金石、碑版的古老能量,来回应内忧外患的现代性危机,重塑颓败的民族精神。这一“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经验中一个极其独特的面向,按汪晖的看法,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文化实践。余友涵对石鼓文的汲取和偏好,虽然基于他自发的一种审美感觉主导,但能够折射出这种现代性文化策略在个体艺术家身上的微观呈现,他接续的,是一条试图在古典资源的再创造中寻找内在超越路径的思想脉络。
再者,我们看到他在童年时接触到的现代艺术,是通过隔壁的邻居范纪曼先生的藏书。而范纪曼先生,是一位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有着直接联系的隐秘人物,其个人藏书的来历,和彼时上海左翼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式和艺术取向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说,他的六个书架构成了一个微型的、充满政治潜意识的“知识库”。这一细节,极具象征性地揭示了余友涵早期艺术启蒙的特殊性:现代主义的审美种子,是通过一条与左翼革命紧密交织的私人渠道,悄然植入其心灵。这绝非一个纯粹的、去政治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起点,而是从一开始就被编织进革命世纪复杂的社会网络与知识流通之中。不同文化脉络、政治立场与美学资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相互渗透、彼此缠绕,无法被清晰的二元对立,尤其是80年代重写艺术史那个过程中的普遍理解方式所简单分割。
还有例子,1956年莫斯科雕塑家完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第二年就运到了上海徐汇区文化馆展览,余友涵就在这个展览现场,直接写生了这座雕像,并且通过头发的处理、基座的省略,把这座雕像在他笔下变得像在描绘一个充满魅力的真人。这座源自社会主义阵营核心的雕塑,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物质化身。余友涵在面对它时,所进行的不仅是造型的摹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与美学的认同。然而,这座雕像的象征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在他塑造之初,或许代表着一种崇高的、不容置疑的革命美学典范;到了1980年代,随着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重新理解,它又被重新的符号化,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与浪漫、建制与反抗之间的暧昧交界。余友涵的早期接触,使得他触及了这一贯穿中国现代艺术史的核心矛盾——如何处理来自社会主义经验的美学遗产?如何在其内部寻找超越其教条化形态的可能?他的敏锐,在于他几乎本能地捕捉到了这些信息,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创作中持续发酵的问题意识。
又比如,余宇刚才说的“丙烯颜料”的问题。我们也认为余友涵的艺术所触及的问题之深广,也会体现在他对于绘画物质材料本身的高度敏感与主动选择上。余老师也曾用过水粉颜料和油画颜料,但这两者都不是他后来最常运用的颜料,这也意味着,他并不对新中国开始的水粉画传统和西方古典传统有着内在的倾慕,因此他没有这些材料尊卑高低的成见。1973年,余友涵随中央工艺美院其他师生一道下放石家庄李村劳动时,同行的老师,祝大年先生、袁运甫先生等都用的水粉颜料,而吴冠中先生等更多用油画颜料,余友涵目击了这个颜料抉择的绘画创作现场。另外,丙烯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跟中国颜料制程的工业化进展也有关系,早期水粉颜料依赖立德粉,而像钛白、煤黑这些高度强色素的提炼技术的进步,使丙烯颜料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成为可能。所以,一个颜料的选择问题,也会涉及很多不同维度的研究角度。
这些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与我们合作的学者,具有“历史化的眼光,同时又有理论化的勇气”来处理这些问题。对余友涵个案的研究,可以也必须向多个方向辐射:往大了说,其艺术生涯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及其文化后果紧密相连;往远了说,其精神源头可上溯至清末开启的现代性文化策略;往近了说,他与年轻艺术家的互动,又展现了历史经验在当代语境中的传递与变异。他正处在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复杂历史脉络之中,其价值在于他几乎无意识地、却又无比精准地,用自身的艺术实践,串联起了这些看似离散的历史线索。
赵剑英:
可以介绍一下今年年初我们委任刘鼎和卢迎华两位策展人策划的深圳美术馆“友涵余友涵”这个展览和相关研究专著吗?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内页
卢迎华、刘鼎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于瀛:
我们在“长乐路的风”这个展览之后,委任刘鼎和卢迎华两位老师筹备这场展览。当然,他们对余友涵先生的关注和研究早已开始,之前在中间美术馆的群展两次收录了余老师的作品,甚至是在2013年,卢迎华老师就撰写了余老师在元空间个展的展评。他们在“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工作方法的核心,在于对艺术家创作生涯进行一种富于理论自觉的“分期”,这并非传统艺术史那种基于风格演变或生平事件的简单编年,而是用一种历史学家的眼光,把他的艺术思想和中国当代思想的不同时期的互动关系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刘鼎与卢迎华对余友涵的研究工作,正是通过分期,将这些不同时期的艺术实践,建构为一个个具有特定历史结构与理论内涵的“问题单元”。他们不是将余友涵的艺术简单归结为形式演变或社会反映,而是视其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实践,其中蕴含着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深刻洞察。我认为他们的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艺术家去世以后,他的创作、他的思想开始变得知识化,“分期”是这个知识化进程的基础工作。他们的研究,在书中呈现为六个长篇章节,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六篇独立的学术论文。当然,这种思想史取向的当代艺术研究方式,也是刘鼎和卢迎华两位老师长期以来的学术风格。
比如,他们论述余友涵80年代开始发现圆这个形式时,常用“道”等具有文化属性的观点,包括宇宙观、文化观放到自己的创作里面,跟当时的文化热存在关系,当然这也是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运动中的一个经典的面向,对“现代化”的渴望包裹在对“民族根性”或“文化本体”的形而上学追寻之中。但同时,这又区别于他的学生辈的抽象艺术家“去意义”或者与中国社会急剧的城市化进程相勾连的表达方式。
又比如,他早期学习西方印象派的风格和技法来绘画上海的风景,余友涵笔下的上海街头,并非对完全是对现实的忠实再现,也非对内心情感的纯粹抒发,而是经过了一种异质的、外来的美学滤镜的折射后,所呈现出的、带有疏离感的“他乡”图景。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体验的核心,本土经验在与外来形式的碰撞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与陌生化效果,也使现实和愿景之间显露出其内在的悖论和潜力。在刘鼎和卢迎华的论述中,这里存在一个如何看待自己现实和美学经验之间张力的问题,因此论文中“青春的异托邦”和“他乡”就在处理这个问题。
卢迎华、刘鼎在“长乐路的风”展览现场,应空间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21
他们的研究不仅仅处理了这类大的判断,也充满了各种旁逸斜出的细节,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地图,上面布满路径与坐标,为后来的探索者提供了一幅精密的“索引”,透过这些草灰蛇线的伏笔,发现新的岔路与隐藏的秘境,开始完全不同的论述架构。从而让这份珍贵的艺术遗产,不断地找到重访的起点。
赵剑英:
我们始终注重从余友涵先生艺术生涯的“长时空”,来理解余友涵艺术创作多变背后的思想,以及他在艺术史中的特殊位置。在此我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年十月份的余友涵先生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由清华艺博资深策展人谈晟广老师策展,展览标题为“大象游形:余友涵艺术展”,策展人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泰斗方闻的学生,过去的研究在中国古代艺术、考古、文明溯源等多有建树,但谈先生也非常关注中国近现代艺术问题,尤其非常关注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在中西比较视域中所具备的现代性潜力,他的研究和刘鼎、卢迎华所采用的理论工具箱、选取的作品,乃至对余友涵先生创作动力和前提的考察之视野非常不同,同样也深具启发性。比如,他通过余友涵先生和高古艺术与书法的内在关联、以及余友涵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艺术思想史脉络的关系,这些都是深具启发性的视角。正如我们的委任研究计划所期待的,不同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在持续的问题化过程中,保持思想向历史敞开的姿态。”
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感谢大家到来这个讲座和我们的新书发布会,谢谢。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