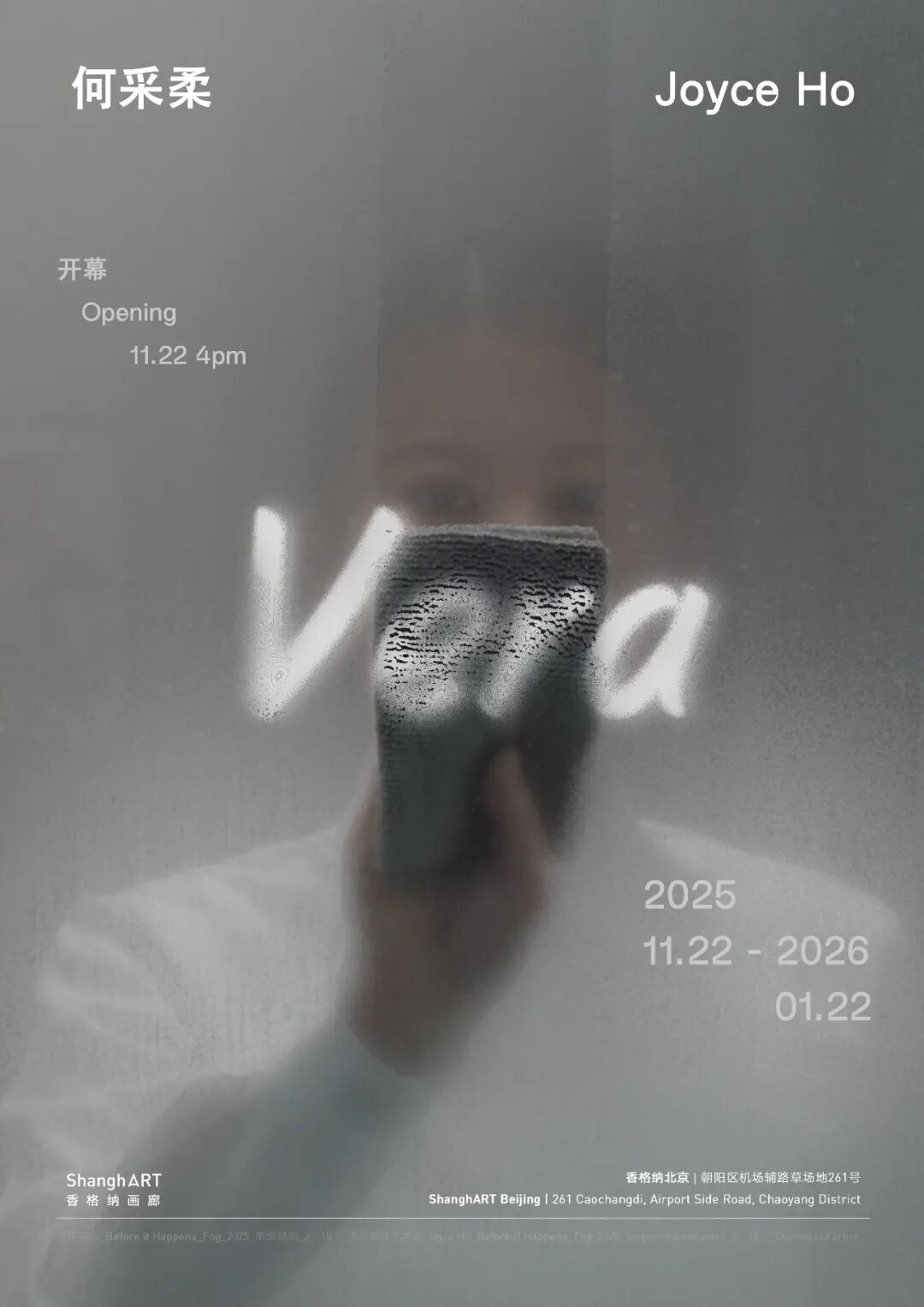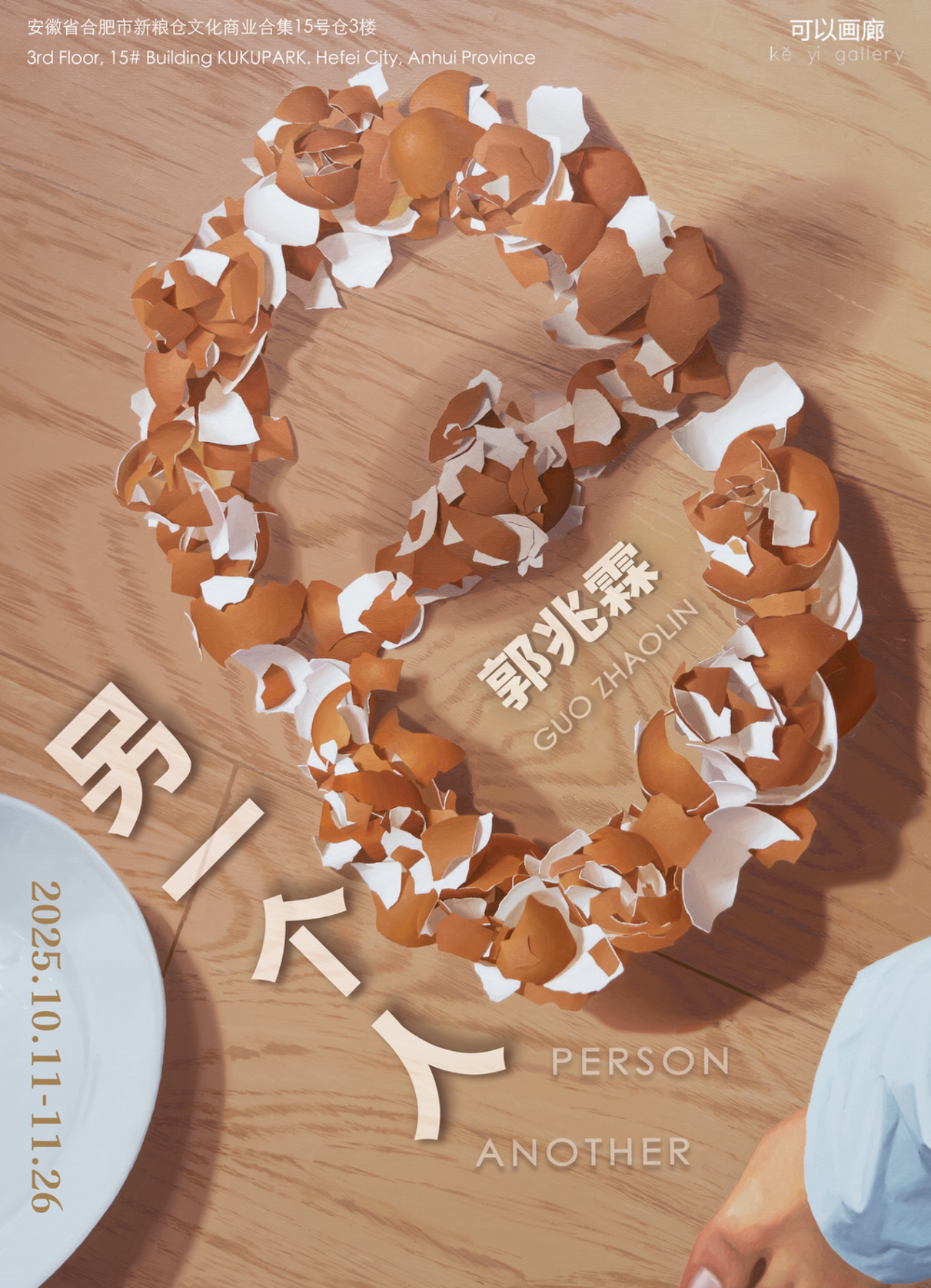摘要:为了洞察复杂图像视觉性的意义网络,对印象派的研究须借助新颖的哲学与艺术理论的交互结构开启智性的问询。“真实经验”是印象派绘画的重要图像特质,借由夏皮罗,该特质由经验感知与视觉反思共同组成。这样的感受性分析旨在呈现一种非话语性的内在智性观照结构,并强调时间维度意义上的“此刻”。而瓦尔堡建构的“情念程式”是通过图像完成对于古代记忆模式的整合。印象派与瓦尔堡在图像心理学层面合流,后者延伸至整全时代心灵的探索。对照以赛亚·伯林等人的阐述,可以认为,印象派呈现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可通往浪漫主义的创造性效果,既要肯定其中蕴含的主观自由精神,还要将个体、自然与历史的张力结构与人类的“整一性”追求相连,从而使人类精神的文明成果呈现更加稳定与普遍的效用。
关键词:印象派;感知;记忆与想象;精神图式;整一性
一、“真实经验”:印象派图像的感知模式
“印象派”绘画是现代艺术的开端,大抵来说,其标志是对文艺复兴所创立的透视、明暗与造型法的重审,体验非固态的流变经验。从印象派的生成进路看,19世纪70年代,艺术评论家路易·勒罗瓦(Louis Leroy)被莫奈的画作《印象,日出》(Impression, soleil levant)所震撼;1877年4月,雷诺阿等人创办名为《印象派》(L’Impressionniste)杂志,为“印象派”这一当时具有贬义性质的评论辩护。伴随马奈在1867年的展览目录前言中坚持表露的工作动力与出发点:“呈现(我的)印象”,人们可以理解,莫奈之所以将《日出》称为一种“印象”,就是在向公众解释这幅画不仅仅呈现一个港口的黎明景象,而更是一位艺术家-观察者眼中的场景效果。这即是说,《印象,日出》拥有自己的可信性,那就是一种真实经验。
经验的真实性成为印象派绘画中蕴藏的一种独特态度,毋宁说它揭示画家主体对瞬间变易性的敏锐感知。尽管中世纪被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描述为一种主要服从于宗教导向的集体文化意象,但在中世纪艺术占据主导地位的神学内容以外,人们还能从中看到世俗历史场景或者寓言、幻想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较于中世纪艺术,印象派艺术对重要主题的呈现围绕两种模式,总体来说,即社会生活领域的环境与功能在基于艺术家的审美、形式与表现效果的协同运作后,在印象派题材的特定主题中予以落实。在《现代生活画家》中,波德莱尔指出,美永远且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其中,时代、风尚、道德与情欲的兼容并蓄势必与“现代性”相连而变为可被多数人理解的艺术类型。这种对现代性之“变易”的集中表达就是印象派艺术,经验感知这一创作品味因此被提升至艺术风格的高度。正如夏皮罗(Meyer Schapiro)所引,基于莫泊桑对美感的描绘,其小说《一生》(Une Vie)借从公海上前往象鼻海岸的女主人公之口说出“在神的创造中只有三样东西是美丽的:光、空间和水”[1],进而:
印象派对主题的选择是能够加以概括的。这些绘画……拥有一种环境意象,这个环境被当作一个运动自由的场域,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感官愉悦的对象。特别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在这种艺术的头十五年里,同时包含观看者和景观的画面比比皆是。画家们被那些真实的场景所吸引……但最初的体验不仅仅是纯粹的视觉,它还包括了太阳和空气的感觉——……触感;味觉和嗅觉的刺激……再加上声音和视觉的刺激。[2]
这段描述较好地概述了印象派艺术家在处理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节主题时所依赖的感受性因素,而这种感受源于一个统一的术语:环境(the environment)。自15世纪以来,环境一直占据着画家们的视线。对印象派画家来说,一方面,他们将环境视为活动场景的延伸背景,在风景中享受感官的自由与协调;另一方面,结合1853年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大规模现代化改造这一社会变革前提,城市景观的巨变被画家群体捕捉至画面。由此,画面的自足性不仅意味着对于自然的研究更加客观与科学,也更加说明印象派潮流并不独立于一般的思想运动,而是与整体性的思想趋势,即批判性反思以及自我审查、自我认识的兴趣密切相关。
既然印象派图像中蕴含着一种与自我反思相关的观念的运动印记,那么,进一步地,印象派艺术最为独特的性质体现在其与先天观念和语言规则相分离的感知体验。对此,贡布里希认为,摄影技术的发明是印象派画家在与传统绘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帮手之一,体现着对于“瞬间”这一时间意识及其所产生的瞬时印象的重视。“只有当艺术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当下此刻的样貌上,他所获得的瞬间印象才能包含着真正的时间维度”[3]——此处,对时间的描述可类比塞尚所称的“小感觉”(petit sensation),最典型的“审美时刻”以包含着易变和难以捉摸的品质与趣味便应运而生。莫奈1902年的作品《雾中的烟:一种印象》(Fumées dans le brouillard :Impression)中通过画中明亮的阳光将烟雾图像表现了出来,将“印象”理解为自然现实与个人知觉的综合,这种综合最终体现为一种对自然性和诗意之美的具体解释:作为一种策略,“印象”一词在绘画具有价值属性,既有美学意义,也有哲学意义,并暗示了一种道德与社会立场。印象派画家在绘制树木的过程中引入看似怪异而不真实的色调,但艺术家们往往可以证明这些色调是真实存在于物体之上的。这种真实性指向了由颜色或强烈光线相互作用的主观效果,譬如,明亮的绿色使人产生了红色的感觉。如果此类画面经验成立,那么印象派的图像风格则具有进入主体感受-氛围美学的可能,具有在复杂整体中进行直接感觉的独特本质。问题在于,在将感觉经验作为知识基础的语境下,印象派对于“心智”的新颖理解与实践如何可能?

实际上,对“印象”概念的历史进行归纳后不难发现,感官印象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对知识的根源——感性印象进行敏锐的分析,并强调了思想对于感官的依赖。必须承认,洛克认为对印象的反思在知识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观念)最足以代表一个人在思想时理解中所有的任何物象,因此我就用它来表示幻想、意念、影像或心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4]这就正如莱布尼茨在评论洛克时所注意到的那样,心灵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外界印象的容器。显然地,莱布尼茨的“观念”概念更集中地表明了其在认识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即“观念是思想的对象……是一种内在的直接的对象,并且这对象是事物的本性或性质的表现。”[5]虽然洛克哲学从经验论立场出发,而莱布尼兹哲学则从唯理论立场出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观念在认识中的中介作用”产生相同认知,进而,意识作为能动的思维形式,通过观念的中介性,将对象把握为“所是”(而非直接呈现为“所是”),意味着以客体为标准的认识逐渐向主体的尺度进行转变。愈发强盛的主体尺度在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观点中显得更为激进。借由电学、化学与力学的物理研究,马赫指出一种新的物与思想符号的关系,“身体是与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感觉相关的触觉和视觉感觉的相对恒定的总和。例如,两种质量相互引起的加速度的力学原理,直接或间接地只给出触觉、视觉、光和时间感觉的某种组合。(然而)它们只有通过它们所涉及的感觉才具有可理解的意义”[6]。在夏皮罗看来,马赫触及到了印象派绘画的本质,世界不是由元素组成的“事物”,而是由颜色、音调、压力、空间和时间组成,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感觉。因而,在印象派艺术中,离散性的颜色、光线比相对固定的事物更显著地体现感觉元素。
从对客观世界的图像再现方式上说,相较于西方近代绘画利用透视法来营造三维空间,利用线条与阴影达成一种写实性,显然地,印象派画家将色彩的重要性置于线条之上。在莫奈这里,外出作画的过程即是不断抛弃对客观对象的记忆的过程,“一棵树、一幢房子、一片农田或任何什么东西,而只是去思考一小方的蓝色,一长块的粉红色,或一条黄色,通过恰如其分的色彩和形态来画出你的所见,”[7]可以说,莫奈跟随着19世纪60至70年代早期印象派制画态度,倾向于将“印象”理解为一种直接给予感知的复杂整体的、个人化的、经由感受调和的综合效果。进而,基于莫奈放弃旧有记忆模型而投奔视觉瞬间感知的选择,对颜色的青睐就意味着从视网膜效应转向一种想象力的刺激。因此,“印象”这一微妙而难以捉摸的感觉所构成的画作不再是一种外观的等价物,而是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构造的东西。如夏皮罗所说,画家对于印象的兴趣仍然服从于更高的理念,后者运行于旧的感知与流动的印象之上,并使二者结合,最终在完整的艺术作品中将其塑造成一种新的形式:“对于塞尚和莫奈来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感觉是一种有意识追和培养的经验。”[8]这一评价体现出,画家的创造力本身已然蕴含着对外部情况的调适能力,是对印象在头脑中闪现的强度与痕迹的显现。
但是,印象派在处置图像的过程中遭遇到的诘问之一亦恰来自于主观感受的无束性。正如梵高一直置身于印象派画家群体当中,是由于“印象派无任何规则要求,不(对画者)施加任何束缚”[9];然而,创作的自由似乎时常惯性式地导致对于技艺精确性乃至图式规则的不假思索的搁置,它使得印象派现象学描述停滞于其瞬间性而失去了其明晰而稳定的整体性。更进一步地,印象派对外部的整体模糊印象在实际感知过程中占有先机,但对这一整体的再现则依赖于局部颜色与的细节化描绘。于是,一种由于视野转换所导致的时间差得以形成,即在观看整体和聚焦于局部细节时,颜色已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致使之前形成的知觉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致印象派获得的并不是某种稳定的整体印象,而毋宁说是类似于不同知觉阶段的视像重叠。作为印象派重要的制图动机,“变易性”不仅是画家群体在二维平面上实现逼真视觉效果的知觉理论支点,使外物直接可见,更因其模糊的不稳定性而牵涉出一种悖论性的结构,发展、转变为保罗·塞尚意义上的对于“普遍性”[10]的追寻。
保罗·塞尚,《圣维克多山》,1906年
在上述概览性描述和理论化探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将印象主义制图模式中所蕴含的个体创造性拓展为对于整一性意识与自由意志的辩证思考,以求立足印象派图像策略的优劣分析,一方面开启对于以阿比·瓦尔堡为代表的古代精神性图式的回望,另一方面则促成对于浪漫主义式自由观念及其界限的探讨。
二、古代精神原型的图像外显
作为对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发展脉络的梳理,贡布里希曾认为,现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克服印象派的变易性,转而重新寻求永恒统一之美,即从瞬间影像走向抽象图式:“塞尚……感觉到因为印象主义者专心于飞逝的瞬间,使得他们忽视自然的坚实和持久的形状。凡·高感觉到……除了光线和色彩的光学性质以外别无他求,艺术就处于失去强烈性和激情的危险之中,只有依靠那种强烈性和激情,艺术家才能向他的同伴们表现他的感受。最后,高更就完全不满意他所看到的那种生活和艺术了……。无论这些运动乍一看显得多么‘疯狂’,今天已不难看到它们始终如一,都是企图打开艺术家发现自己所处的僵持局面。”[11]让经验感知变成稳定图式,并推动图像参与“变易”与“永恒”的结合,这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重建绘画图式的主要道路。将印象派的“变易效果”置于胡塞尔的哲学框架中,则体现为其对纯粹感知的重视。在胡塞尔那里,不同音符的接连关系基于人对每个音符的感知,感知会延续一段时间,再逐渐衰减并蜕变为回忆和想象。通过前一音符所引发的对后续音符的预期,瞬间性辐射出一幅“时晕”图景,其中留有对原印象的滞留与前摄(protention),从而形成有保持和预持深度的绵延时间之流。进而,相较于回忆和想象,感知乃是一种原初性的行为:
它(感知)将某物作为它本身置于眼前,它原初地构造客体。与感知相对立的是当下化,是再现,它是这样一种行为:它不是将一个客体自身置于眼前,而是将客体当下化,它可以说是在图像中将客体置于眼前,即使并非以真正的图像意识的方式。[12]
对印象派而言,直观感知具有极大的视觉强度与吸引力,因此,他们强调在户外作画,在此过程中,外在世界呈现为斑斓的瞬间影像。而当回到室内,尽管感知可以滞留的方式得以绵延,但迟早将转化为回忆与想象,从而使得画家最初捕捉的原初印象褪色、变形。可以看出,在印象派的图像语境中,“此刻”这一时间维度无时无刻不镌刻在画家们的意识之中并指导着画面的创作动机、过程与方式。
克劳德·莫奈,《干草堆》,1891年
然而,不难看到“记忆”问题在印象派画面生成动机与方法论意义上的失效。更为关键的是,记忆不仅停留于古希腊罗马至今的背诵技艺层面,以柏拉图《斐多篇》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背诵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记忆受到诋毁,启蒙理性压倒记忆而成为胜者。因此,记忆问题离开了纯粹的学习记忆(Lerngedächtnis)范畴,而更加深入到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意义上的宽泛文化传统之中,成为联结个体与民族的一种修养记忆(Bildungsgedächtnis)。因此,记忆难题从未真正地自行消解,而是在不断得到强化。与前述相对应地,得以强化的部分并不是雄辩术的记忆术,而是基于心理学的传统,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回忆功能的重释:“把记忆看作心灵的三种力量之一,称其为内在知觉(innere Sinne)。(雄辩传统)针对的是知识的组织和图示化的秩序,(心理学传统)关注的是记忆与想象和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13]由此,记忆作为一种“力(vis)”而非“术(ars)”广泛地存在并波及时代文化的诸多象征领域——而当对记忆的处置从经验史跃迁至文化史,特别是当过去的回忆就在当下被重新激活,拥有情感与心理的双重维度时,艺术图像所承载的精神被视为一种具备与古代发生神秘共振的文化整体。在此意义上,由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掀起的图像学潮流成为文化史与思想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记忆形态与瓦尔堡提及的古代图像中抽象之“力”对直接对象的影响紧密相连。具体而言,不可见之“力”以“痕迹(trace)”的形式呈现出来,后者伴随着具体现象,并在瓦尔堡的“情念程式”(the Pathosformel)和“动态图式”(the Dynamogramm)概念中聚焦为对情感的动力形式的关注。最为根本地,“力”的辩证形态涉及到如何处理过往,即“历史(das Historische)”的问题。其中,关键的观念域之一即“文化可塑性(dieplasticsche Kraft)”及其辐射开去的记忆问题。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批评巴枯宁出于对现在的仇恨而想要摧毁历史与过去的认知,并提出一个非凡的假设:(如果)记忆和感觉是物质性的(das Material der Dinge)[14]。此处,尼采意在强调一种可塑的物质性(plastic material),更是一种能够进行各种形变的材料。这种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既定综合的原则使得对于文化史的理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内部,普遍性将能够根据特殊对象的所受到的每一次冲击或者压力的变化而改变其形式。吉尔·德勒兹称之为一种“高级经验主义”(superior empiricism)。这种经验主义在瓦尔堡的思想脉络中被实践为一种具有极性特征的能量。
1923年4月23日,瓦尔堡在精神病院做了一次有关美洲印第安人蛇舞仪式的讲座,筹备演讲的笔记和草稿揭示了瓦尔堡回忆其求学时期关于人从魔法恐惧中解放出来的种种观念[15],它们将协助瓦尔堡在遍历自然万物的杂多形象后经由自我整合而导向一种艺术或曰精神之“原型”(Urbilder),后者在各类图像生成的过程中亦能够返回人类整全的精神本质。因此,瓦尔堡强调,若单以民俗知识或生物学立场去理解羚羊舞,进而嘲笑人种学中的滑稽因素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立刻关闭对那些悲剧性因素的洞察力。此次演讲是瓦尔堡在文化心理学与人类学领域走向成熟与突破的标志,因为其核心观念“情念程式”已被纳入“遗存”(Nachleben)的范畴加以思考。即是说,“情念程式”并非单纯的形象或形式,亦非简单的身体姿态的语义学与符号学,而是与心理症状相交互的情感能量的固化。通过对原始人的考察,瓦尔堡认为,自然力量不断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最初的状态是恐惧的状态。然而,在人类将这种恐惧转化为记忆时,后者变为一种积极的、具有动力性的能量,人类正是凭借记忆功能,将本能的恐惧反射用已知图像——无论它多么可怕——代替对未知原因的恐惧。这是人类文化功能对未知恐惧赋予的心灵超克之力。因此,应该摆脱对于瓦尔堡著作所做出的消极判断:分散、微观、缺乏稳定性,而要正视瓦尔堡知识序列间蕴藏着的可塑性,它们通过记忆和交错的变形发挥作用。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所倚赖的“图书馆计划”及数量惊人的手稿、卡片与文件共同构成的是具有“再生性”的材料,它们不仅有助于图像风格的积累、推动“好邻居”原则的施行,更通过图像来展现精神的极性结构,将人类生命史转化为一部储蓄与铭写心灵动能的情感史。
对于瓦尔堡而言,在古代艺术史的语境中,作为涉及到情感与心理的观念无时无刻不作为艺术图像创制的核心标准而指示着具体的创制动机。为了更好地切近艺术与图像的“属人性”,今日的艺术史研究通过图像这一可见的形象基础与历史材料重赋自身活性,而这种活性又倚赖对图像内部活力与能量储蓄的确认。尼采哲学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关联成为其中一种可能的思想来源:图像是主观情感的客观化。这就是说,以音乐为代表的酒神精神沉浸在不断变动的漩涡之中以逃避存在之苦,以造型艺术为代表的日神精神则凝视存在的形象,并用一种象征型的梦境图景,将酒神之悲苦转换为幸福。最终,日神的静观充分统摄了酒神的动荡,同时意味着承认图像所具有的内爆潜质。尼采的格言“从形象中得解救”成为图像内部丰富蕴藏的注解。1906年,瓦尔堡将整个文艺复兴描述为“狄奥尼索斯式的亢奋(Dionysian stimulant)”与“阿波罗式的明晰(Apollonian clarity)”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所昭示的“古典的不安”被瓦尔堡视作古代艺术和文化的本质特征,而十四世纪的意义在于它知道“如何赋予古代异教世界双重内容的艺术价值”[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瓦尔堡将尼采和布克哈特视为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不仅是其所解释之时代的主人,更是作为这个时代内部所隐含着的时间(implicated time)的主人。瓦尔堡将地震仪(seismograph)这一概念赋予布克哈特和尼采。作为一种技术设备,地震仪尤其记录那些看不见的、无法感受到的运动。但与此同时,这种内在运动的进化也将以一种超乎视觉与身体把握的方式成为一场摧毁万物的地震。对照于精神世界的震荡,布克哈特和尼采正是以此方式记录并讲述着内部时间中的起伏的某种“助想波(mnemic waves)”[17]。因此可以理解,在瓦尔堡眼中,拉奥孔的静默塑型并非雕塑受限于静态母题和固定的视觉符号[18],反而成为其情绪崩解的注脚,是由于古物所携带的记忆对沉思与迷狂这两种精神活动极点的包容,“这种二元对立产生了人类智识上的困境,它构成文化科学的真正主题,并将所描绘的居于冲动与理智行动之间隙处的精神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人类遗存下来大量源于恐惧的印象。正是在对这些印象‘祛妖魔化’的过程中,情感表现的全部可能性被容纳了进来。”[19]
由于人类学与文化心理学的深度介入,古代图像的艺术性获得了新的阐释维度。可以说,瓦尔堡意义上的情感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当人与世界交互时,前者如何应对后者本身的威胁性及其所生成的创伤性。在这个过程中,人展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制服,只是这种克服将首先被人类内化为某种防御性的“治疗”经验。另一方面,“极性结构”固然具有其历史普遍性,但是,当古代的情感能量嵌入到每一个具体时代的集体记忆中时,有些能量会被强化,以至定向为图像表征;而有些能量则会被弱化,等待在另一个时代予以重新激活。这种能量传递与表达机制最终落实为瓦尔堡“古代遗存(Nachleben der Antike)”观念。这里,瓦尔堡的博学与智慧展现为他并未被一种“因果关系的本能”所蒙蔽,而是能够为未知和陌异留出空间。因为瓦尔堡看到,古代的情念程式在古典时代结束后并未宣告消失,而是以诸多变形的方式继续留存在各个时代的精神文明书写之中,成为迪迪-于贝尔曼意义上的历史的“症状”:
在我们所建立的语境之中,它是遗存之事物所发生的非常具体的律动:突然的开放[侵入](现在的涌现)与复返(过去的涌现)的混合。换言之,这是一场意外的冲突(逆时间性)与重复的共存。[20]
在此,对古代记忆的可塑性以象征性的方式被完全显露出来,体现瓦尔堡深受尼采启迪的“古代遗存”的奇异辩证法:一方面,必须处理对古代事件的回忆问题,因其是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此时此刻处理遗忘问题,因其是构成人类行动的重要原因。其中,有选择性地回忆与遗忘均属于“记忆”的范畴,而人类在受到历史“极性结构”牵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是一场变化与运动的游戏、一种力量的关系。历史的症状就是时间的移动与激荡,在这里蜿蜒曲折,在那里则锋利强硬。正如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作为美学领域的两种力量那样,其相互作用使文化精神的运动成为可能,从而使生命兼具“生命活力”(ein rätselhafter Organismus)与“生命能量”(Lebensenergie)的双重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史始终存在于“力”的纽结之中,并处于人类文明史的漩涡中心。
三、 作为自由边界的图式整一性
在经历哲学化的理论运思后,应在一种主体与外部的联结场景中理解印象派艺术中的感觉元素。在印象派画家进行创作的过程中,经验性的感觉体验固然是第一性的,但因循夏皮罗的逻辑,哲学性的反思因素并未退场,而是更多地在知觉的中介中延续一种通向自由本能的审美动机,这体现为印象派画家在践行视觉感受的过程中,亦将自身与外部世界相联通,在对世界的体验是“与自我连贯一致的大量感觉”的基础上,印象派绘画与实存世界的关系避免成为一种以自身全然独立状态被确切把握的孤零结构。因此,德拉克罗瓦会相信,如果心智是从感觉到更高形式的知识的建构,那么印象本身就是创造性人格的起点。
克劳德·莫奈,《韦特伊教堂的雪景》,1878年-1879年
所谓“创造性”,更集中地体现为印象派通过减少乃至完全取消立体造型,从而摆脱由庞大的对象形式引导的笔触,特别是在早期印象派绘画中,画家把光、空气、运动、形状和颜色都用笔触清晰地构成一个整体。笔触的整体性一方面使得印象派画家实现了真实形象,另一方面,画笔痕迹的复杂性质亦挑战传统的视觉完形习惯——莫奈《韦特伊教堂的雪景》(The Church at Vétheuil, Snow, 1878-1879)中无形状的笔触、罕见的色调以及混乱的形式交织编出一个连贯的整体。可以理解,雷诺阿强调的“看画必须保持一臂距离”旨在将图像客体的外在可辨性和审美主体的内在生命性进行联结,以刻画出一个由触蹦(stroke-bound)和刷痕(brushmark)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乃是客观样态与主观激情的共同映射。
虽然同样瞄准笔触、色彩和光线等重要的图像构成元素,但对于这一印象派式的感知分散与整合方式,鲁道夫·阿恩海姆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最集中地体现为把握事物整体结构或同一结构之上,毋宁说从本质上揭示了印象派依赖瞬时性与局部性的主观性。在阿恩海姆看来,印象派的画中世界显示出一种内在的明亮光辉,而这种效果得以存续乃至放大的前提源于物体轮廓线的模糊性质。于是,画面的质料就是涂在画布上的色彩和式样,这进一步导致了物体看似的非透明性,并促成内部空间的游移性。阿恩海姆对光线的执着同时表现为一种视知觉与心理学分析方式。从心理学的范围而言,眼睛所感知到的总是反射亮度和照射亮度相结合后所形成的亮度,即人们所看到的眼前事物的亮度“主要取决于整个视域之内亮度值的分配状态……取决于它(光线)在某一特定时刻所形成的整个亮度梯度中所占的位置”[21]。这就是说,对物体的认识从来都是通过比较而非区分得出的,而光线成为这一识别过程的关系介质。正如阿恩海姆所归纳的,印象派图像的光线运用使得绘画为眼睛提供一种其在物理空间中所能接收到的单一刺激,对于视觉理解而言,这种单一性无疑是理想的,因为“(画面)各个层次的分离就会由观赏者自己的知觉产生出来”。具体地,19世纪印象派画家们所运用的想象方法对画面上与物理空间中的照射作用起到了统摄的效果,绘画“由单一的亮度值与色彩值构成”就意味着光线与阴影的对照关系被纯粹的内部光源系统所取代,在视知觉层面,艺术创作与自然景致之间不再有所区分。但与此同时,阿恩海姆又一次指出了对瞬间成像方式的担忧:
印象主义派致力于把人类视觉认识能力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活动中。……但它的方法(即“记录最小色彩单位”)却有可能使艺术家面临着既失去客观事物又失去绘画形象的危险。按照这种方法画出来的画,全都变成了相同单位的连续体;……整幅画画的是一种东西,同时又是这种东西的无限连续。如果把这种方法发展到极端的话,“生命的机体组织”就有可能不复存在,形状和物体也就会随之消失。[22]
看来,使形象彻底摆脱客观事物的形态,从而只服从于人的视觉理解力,毋宁说是对“生命的机体组织”的损伤。视觉的一瞥无法代表事物的整体,而多个“一瞥”仍不过是各个互相矛盾的形象的集合体。其中,表现性中的重要因素——“力”——完全藏匿于主观创作与客观世界的同质化关系之中;对印象派绘画而言,生命的张力运动逐渐弱化为平均分配的光线强度。这种图像的均质效应在阿恩海姆处被进一步推向一种有关“平等”与“和谐”的艺术风格反思:
这样一来,它(点彩派的色彩斑点)就更加激烈地排斥了“有一个从外部向内部照射的光源”的观念。相反,每一个点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光源,整幅画就象是一块布满了闪光灯泡的平板,每一个灯泡都发出了同等强度的光线,每一个灯泡都自成一体,不与其他灯泡发生联系。在这个高度民主化的集体中,最高原则就是平等与和谐。[23]
让图像内涵具有生命活力的属性,实则是将图像视为思想的视觉框架,而力的结构则成为内在精神表现性的运行根基。印象派似乎在面对超自然观念上保有一种现实化立场,画家的主体性仍很大程度上受缚于客观世界的影像。夏皮罗会发觉,19世纪中期的风景品味被解释为一种泛神论观点,海洋体验在与宇宙意识的相遇中演化为对无限自然的直接理解,以取代或补充对超自然的个人上帝的虔诚宗教意识。对艺术家来说,绘画中的天空和海洋往往是组成当地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乃至成为玩耍的安全港和度假圣地。特别是对于莫奈而言,海景画的演变意味着海已然失去了崇高尺度和感觉的压力,“莫奈也许喜欢埃特尔塔和贝勒岛的水和巨石,但在他的艺术中,他很少关注弗里德里希、库尔贝和浪漫主义诗人所体验的一种无限的整体性”。[24]
乔治·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1886年
相较于印象派在热爱自然与不断驯化自然的过程中寻找一种现代生活的惬意,对“无限的整体性”的追求则体现了18世纪以降的德意志浪漫派探索人类认知能力和艺术审美能力的雄心。虽然印象派与浪漫派均通过不同方式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主体意识的自由性质作为一种显明的思想风格进入到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之中;然而,19世纪80年代包括修拉、高更和西涅克在内的印象派团体开始偏离印象派。一方面,以雷诺阿为代表的艺术家重新被安格尔、普桑等法国17世纪的艺术大师所吸引,从对人物自发运动的感知回归到传统形式主义,其《大浴女》(1887)便是范例;另一方面,以左拉为代表的小说家、批评家指出,80年代的印象派已经变成阳光和大气的技术精湛的描绘者,在画作中无视人性元素、苦难经验乃至时代意识,只处理中立于人类条件的视觉片段。因此,夏皮罗会认为,印象派的模式在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加剧的紧张、神经质和焦虑状态时仍缺乏解决冲突的能力:
对新一代来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能够引起一种更为自信的态度,引发一种环境中的独立、力量和欢乐情感的价值,到了1885年开始成为认识自我和理解社会的障碍。印象派甚至成了被动、默许和浅薄的象征。后印象派无法再将以前的观点和一个社会里的经验模式当作艺术的沃土。[25]
这段内容概括了诸如图卢兹-劳特累克、雅米·恩索尔(James Ensor)与爱德华·蒙克在图像风格上对印象派的反叛:他们或将令人心旷神怡的阳光海滩改写为月亮在海面上的孤寂投影,或将度假城市视为被野蛮疯狂甚至终极死灭的情感聚积地,或将欢快的集体活动建立于个体的解体之上。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大浴女》,1887年
实质上,这种反讽的视觉转译意味着在处理外部世界的可见性当中,置身艺术创造过程并认识自我的信念,转型为对于内在自我中心的情感图式的回应。也就是说,在印象派对环境及其产生的光影冲突的不同记录中,充实的外部生活图景逐渐变为对内在世界的幽暗情感的观察,生命感和存在感的重点从外景挪到内心,暴露出一种受到整全时代精神(Zeitgeist)所吸引的艺术特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瓦尔堡很少从单纯形式或知觉层面理解艺术风格的原因乃是由于图像并非一个潘诺夫斯基意义上自足并等待破解的所指库,而是要将其放置在互文性语境之中,关注图像意义及其价值在图像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中的演进与变形。“图像之于他(瓦尔堡)只是通向文化深处的中介,图像是时代文化的症状,图像与文化是通过隐秘的精神象征联系在一起的”[26]。可以说,瓦尔堡艺术史立场中对宏大心灵性的关切承继了兰普雷希特的主张,将艺术史用作了解一个社会的心灵中的观念(Vorstellungen)的特权与手段。
相较于瓦尔堡强调在附饰运动中捕捉永恒的生命形象,印象派绘画的“即时性”则意味着画家着力捕捉事物的瞬间成像,而这种影像的生成仅仅依赖于感知,于想象和记忆无涉。然而,在瓦尔堡对“时代精神”的艺术性揭示中,永恒的生命形象并不存在于宏大而显著的图像主题之上,而是经由一种“附属的运动形式”完成传导。其中,附饰细节表现出的美感仍是表象,真正使瓦尔堡感兴趣的是细节在图像中以此种形式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由此可见,对于图像功能的重写意味一种深刻的心理主义前提。比如,在T·J·克拉克看来,阿比·瓦尔堡的“你活着,却对我无能为力(Du lebst und thust mir nichts)”直指人类最根本性的恐惧。这一警句在于揭示一种颇具悖论性的图像学知识:若干世纪以来,西方艺术深知为了除掉一种事物的神秘力量,可以耍一种伎俩,即将生命注入其中,以除掉它先天所带有的死亡力量的恐怖面具。[27]对于瓦尔堡来说,图像不仅仅依赖视觉。最初,“看”的行为仅是作为日神光辉刺激眼睛的的结果;然而,在酒神状态下的视觉受情感系统的激发与增强,释放所有的表达:表现、模仿与变形。因此,“看”不仅是行为,更成为需要知识、记忆与欲望的一种能力,而整个视觉能力体系将主体纳入其整体感官、心理与社会之中。
可见,印象派绘画不予依靠的记忆与想象反而在以瓦尔堡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传统中始终受到重视。浪漫派艺术史观的先驱赫尔德在谈及人类趣味变迁的历史观时,提到一种被以赛亚·伯林称作“表白主义(expressionism)”的观念,它区别于十八世纪美学对于艺术作品价值的认定方式——后者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其自身决定的;而在赫尔德看来,艺术作品是某人的一种表白,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观者与创造者之间发生某种接触与对话。进一步地,人的表达依赖词语,而词语“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经由传统意象代代相继的长流水……这条长流已经容纳了别人的情感表白。如此一来,个人就与他人共饮一水”[28]。于是,具有同一民族(Nation)特性的、细微的共同心理模式将图像的纯艺术属性提升为对于人类智性发展史的概括。简言之,赫尔德所理解的图像功能建立于一种“民族根性”体系之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想,而寻找并理解其“文化重心”成为不同理想根基获得穿越时空之动能的保障。在此,审美意义上的“永恒性”与文化史意义上的“整一性”均得以浮现。
进一步地,在浪漫派的语境中,对“整一性”的理解往往与“无限性”合流——这是印象派艺术较少重视的一种理智直观。浪漫派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探究绝对同一性在个体、社会乃至国家层面的创造与应用。那么,艺术图像既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亦作为一种样式被提升至理智启蒙渠道的高度。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指出,“艺术”与“真理”在认识论层面具有互文性,继而既成全了真理的唯一性,亦满足了艺术的多样性:
真理的本质需要做何种变化才能使艺术不再排斥于真理之外?真理不应该再被理解为对象的再现或再创造,而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主动自我实现。这一实现在对象构造中可以是无意识的,而在艺术作品中可以是有意识的。……在美学中,自然概念没有完全被理解:自然概念不是指外在的东西,而是指内在的东西:即主观性的创造力。……由此,艺术在其真实显现中获得了它所特有的不可阐释性(“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无限性经验表现;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相互理解状况的不可解释性以及我们的存在本身的神秘性也正体现在艺术语言的多义性中。[29]
因此,印象派对于“感知”的忠诚及相应地对于“回忆与想象”的平淡化处理似乎无法更为透彻地揭示在历史进程之中的“心灵图像”,后者强调图像既拥有印象派意义上的现象学式观看结构,更能唤起观者的沉思活动,进而在历史感和共通感中体察一种文化史层面、稳固确定的精神本质。历史学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针对图像学方法的哲学反思所切中的正是图像与精神之间的表里关系。在《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中,沃格林认为,领会图像的最初方式往往始于“主题、构图、各种色值及其平衡、技法、以及与其他画作的比较”——一种印象派式的感知分析模式,而非“在凝视中同时还将其注意力转向时间之流动”。关键是,仅仅借由眼睛扫视而对一幅画所作的统觉(apperception)的功能“是充作感官导引(sensory entrée)[带领人]进入精神领域(spiritual realm);但是这个精神领域与时间的流动没有任何直接关系。”[30]那么,只要解到人类意识的功用乃是远离它自身即逝(vanishing point)的点,看到“流动”的兴味,即构成由意义、道理、灵魂之秩序形成的非空间与非时间的世界,就能够避免由聚焦于即逝点所带来的困扰:“不仅不会更好地理解作为整体(whole)的意识与时间,反而让人将躯体领域领会为意识的根子所在。”[31]可以看到,沃格林是将图像视为一种超越单纯时间性与身体性的文化征象,其中蕴含着人类的心灵完型结构,从而使得诸如注意力、意识视野、联想与回忆的丰富程度成为理解图像的拓展性知识,最终呈现为一种“内在照亮(inner “illumination”)”的特征——能在过去与将来这样的内在维度中被体验到。在此,人类的智识活动既表现为对图像的知识性意图的成全,亦表现为图像观者与作者之“间性”的思辨模式,更表现为人类文明活动与生命活力所归至的普遍历史秩序。
结 语
鉴于图像在可见与不可见之两极摆荡的暧昧性与繁复性,若单纯将其规定为一种可见的理智性结构,将有可能落入独断主义的窠臼;反过来说,在针对回忆与联想这两种无法直接显现于形的维度上,如何保证不可见之艺术和历史意志仍作为图像生成的秩序性保证,皆是关于印象派放弃过往时间维度一问的延续性思考。借由保罗·利科的诘问,“主要问题不再是知道我们如何从心理上(或物理上)再现事物——当它们不在场时,而是我们如何创造意义。我可以这样说:语义创新如何成为可能?”[32]桥接康德意义上的创造性想象——一种以《纯粹理性批判》中判断力的综合为标志的想象模式,在利科的语义创新中,想象仍处于首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语义的创新亦衍生出多重影响,其中较为关键的是语义创新要受到“图式”这一规则的支配。对西方现代艺术而言,塞尚、梵高以及高更三人分别对应的客观图式、主观图式与超验图式[33]均试图对感知的变易性进行一种调和。虽然这一中和行为通过图式对自由的主体意向进行约束,但却令艺术疏离了普遍审美。为了寻求“整一性”,瓦尔堡的“回忆”学说重返图像阐释的体系核心。简而言之,在瓦尔堡自创的复合词“pathosformel”(情感范型)中已然包含着一种垂直于艺术史发展历程的时空纵深感,是极为原始的生命情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传递性。因而,在于贝尔曼看来,瓦尔堡所描述的“无名之学”揭示的乃是一整套古代记忆的情感能量学,也是可见的图像症状与不可见的人类历史心理学的摺合装置。至于图像整一性问题是否可上溯至诸如德意志浪漫派追求世界的同一性本质或自由边界等议题,则期待有识之士继续探讨。
注释:
[1]参见居伊·德·莫泊桑:《一生》(Une Vie),in Romans, Paris, 1959.
[2]迈耶·夏皮罗:《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16-17页。
[3]苏宏斌:《时间意识的觉醒与现代艺术的开端——印象派绘画的现象学阐释》,载《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4页。
[4]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
[5]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2页。
[6]Ernst 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xposition of Its Principles, translated by Thomas J. McCorma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06-507.
[7]易英:《三十二个展览:印象派全景》,上海博物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页。
[8]迈耶·夏皮罗:《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50页。
[9]Johanna Van Gogh-Bonger.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 with reproduction of all the drawing in the correspondence: Volume 3.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1958.pp.45.
[10]关于印象派高度私人化的创作立场及其所面临的“普遍性”困境,可参见针对塞尚研究的著作两部:Merleau-Porty. Maurice. “Cézanne’s Doubt.” The Merleau-Porty Reader.Eds. Toadvine, Ted, and Leonard Lawlo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 pp.65-85;【英】罗杰·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沈语冰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6-9;78-81页。
[11]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554-555页。
[12]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4页。
[13]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14]Georges Didi-Huberman, The surviving image: phantoms of time and time of phantoms,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 trans. Harvey L. Mendelsoh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7. pp. 94.
[15]E.H.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6页。
[16]Georges Didi-Huberman, The surviving image: phantoms of time and time of phantoms,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 trans. Harvey L. Mendelsoh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7. pp. 89.
[17]Georges Didi-Huberman, The surviving image: phantoms of time and time of phantoms,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 trans. Harvey L. Mendelsoh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7. pp. 67-68.
[18]参见E.H.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7页。
[19]阿比·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导言:往昔表现价值的汲取,周诗岩译,载《新美术》,2017,38(09),P44。
[20]Georges Didi-Huberman, The surviving image: phantoms of time and time of phantoms,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 trans. Harvey L. Mendelsoh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7. pp. 103.
[2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李泽厚主编,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14-415页。
[2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李泽厚主编,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
[23]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李泽厚主编,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51页。
[24]迈耶·夏皮罗:《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124页。
[25]迈耶·夏皮罗:《印象派:反思与感知》,沈语冰、诸葛沂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423页。
[26]吴琼:《“上帝住在细节中”——阿比·瓦尔堡图像学的思想脉络》,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1期,第20页。
[27]T·J·克拉克:《瞥见死神》,张雷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36页。
[28]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张箭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29]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105页。
[30]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31]埃里克·沃格林:《记忆——历史与政治理论》,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32]保罗·利科:《想象与隐喻》,赵娜译,载《文艺美学研究》(2016年春季卷),第297页。
[33]关于塞尚三人的图式类型归纳,参见苏宏斌:《时间意识的觉醒与现代艺术的开端——印象派绘画的现象学阐释》,载《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8页。

作者简介:王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曾赴法国巴黎艺术史研究中心、美国夏威夷大学等地访学交流。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围绕美学、图像问题辐射到的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