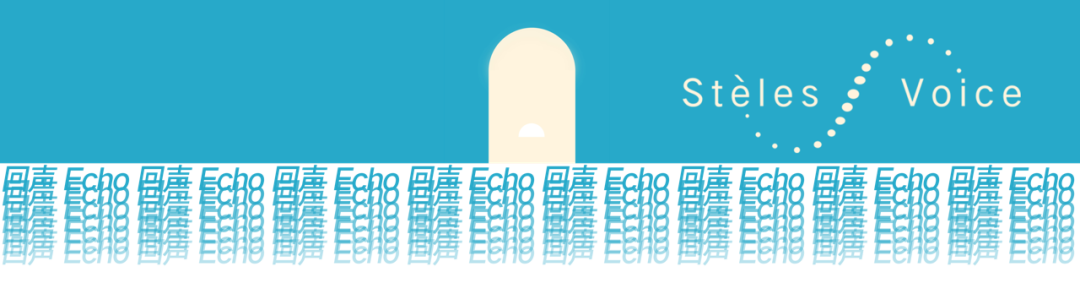
文化精魂的再造与重构
刘丹、邵帆和徐累
文 | 魏 祥奇
(美术学博士、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如果说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现代水墨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接受西方现代艺术史以来的语言、思想和观念启发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水墨面对的紧迫问题则是民族文化身份自觉的问题,即如何在语言和观念上,将现代水墨取得的成果实现中国化。显而易见,这一转变并非是水墨艺术内在的驱力推动的,而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语境决定的。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接受中国水墨艺术的影响,有艺术家仍以水墨为媒介进行创作,但欧美等其它国家的艺术家基本上没有接纳,甚至是没有接触水墨:水墨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和思想系统,只在极少数的欧美学者圈子内引发关注。
2013年,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策划的“水墨艺术:当代中国的过去作为现在”,也让我们真切看到欧美国家对当代水墨艺术的态度:中国艺术家应该摒弃水墨的文化内涵,积极汇入到西方当代艺术的生态中去。这也就时时刻刻警醒水墨艺术的创作者们,既要审慎地保持与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距离,也要注意保持与西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差异。换而言之,当代水墨艺术创作必然要在激活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借鉴西方当代艺术视觉和理论两个体系下展开自己的工作,获得新的平衡,才可能让自己活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西方当代艺术视觉和理论多彩纷呈,并非定势,如何折衷中西,甚至是融汇古今,撷取菁华而自成一体,是当代水墨艺术创作者必然要面临的基本论题。一言以蔽之,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知识系统中重塑自身的精神,而必然面对的是一种游牧的文化和思想形态,一种伴随着殖民话语、后殖民话语、东方学、亚洲主义、民族和国家、中心和边缘话语的历史谱系。
不仅如此,我们在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结构中发现很多源于东方文明、源于中国文化根脉的影迹,这在亚历山大·门罗“第三种思想——美国艺术家凝视亚洲(1860-1989)”的展览中得到更深入的印证。也就是说,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者说自航海时代以来,甚至可以说自文艺复兴以来,及至更早,从来就没有决然的中西方之分。在远古,全人类更是共享着相近的传说和英雄史诗,同样,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也一直在汇入着周边民族和国家创造的文化源泉形成的涓涓细流。就像中国现代水墨和当代水墨,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其完全得益于西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启发,但对其内在精神的阐发,则有着大不同于后者理论体系的言说空间。更有研究者和创作者在西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理论话语中,析出与中国文化精神相通的思想观念,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在19世纪以来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反哺的结果,以至于认为中国现代水墨和当代水墨的语言和思想,正是生长于中国文化精神土壤的滋养之中。就像西方现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中的表现主义艺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极少主义艺术、偶发艺术等,其中都蕴含着中国文化的质感,乃至于由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共享的东方艺术的精神特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日本和韩国较为深入地接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影响,出现了井上有一、白发一雄、关根伸夫、李禹焕、白南准等享誉世界的艺术家,虽然他们的艺术极具有西方当代艺术的视觉表征,但中国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和艺术家都肯定地指出他们的艺术中有着鲜明的日本文化气质、东方文化气质,是远不同于西方当代艺术史创作逻辑的日本经验和东方经验。以至于有很多中国艺术家积极接受他们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些日本和韩国艺术家的作品中感受到相通的思想经验,而这种思想经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亚洲和东方的文化和思想经验,其意在于将自我置入此思想情境之中,进而获得自身话语形态的国际性、传统性两个维度的延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来没有一位水墨艺术家主张完全接受西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影响,进而将水墨仅看作是一个语言媒介,忽视其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联性——之所以他们选择水墨而不是油彩或者其它语言媒介,正是由于水墨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卓越的艺术家总是非常注重自我独特的思想经验和文化经验,尤其是试图要与西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史同台竞技的艺术家,他们既要掌握西方世界所熟悉的当代艺术语言和形式,更要有超越性的思想的深度。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些艺术家往往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身份意识:这与他们所经历的后殖民话语体系的塑造有着紧密的联系。抑或者说,后殖民话语是中国艺术家走向西方世界时必然要经历的一种思想结构的改造,这一历史和思想是前置的形态,进而使所有的亲历者都得做出回应,不可以直接略过。就像中国当代水墨艺术要想走向世界艺术史舞台的中央,就必须摆脱这种历史和思想话语前置形态的困扰。如果说在新世纪之初一位水墨艺术家试图绕过这一论题,几乎是匪夷所思的,这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综合性的历史语境决定的;而今天,则有越来越多的水墨艺术家显示出高度的文化自信,他们在西方当代艺术的视觉谱系之外,建构了一个新的视觉和思想场域。在这里,他们更为注重阐述中国文化精神内在的活性,他们在水墨艺术的自然性和精神性中,找到对抗资本主义伦理、对抗精神分裂的新路径。受邀参加此次“极地清晨”展的三位水墨艺术家,正是站位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创作中展现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超越西方当代艺术设置的理论陷阱的新的感知态势。
刘丹最早接受新金陵画派画家亚明学习描绘现实生活的新国画,1980年代初便移居美国,尽管他没有参与国内现代水墨、实验水墨的展览活动,但身在美国的他,却广受到美国酷爱收藏中国古物的藏家的推重,进而创作了一系列描绘中国古物,尤其是以照相写实的手法用水墨绘制的山石系列,可谓触及到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起点。自然,美国藏家在刘丹的绘画中看到的是水墨艺术的至精微的绝技,但在刘丹的理解中,石头的纹理中隐藏一个超游象外的精神世界,在像静物写生一样的摹绘过程中,他会进入一种眩晕的状态,通过游动的笔触,去感知浑沌生成之际,天地万物凝聚成形的初始形态。最初,刘丹画带有强烈抽象意味的山水画构设画面,但最后他在山石中发现虚实相生之理,以至于他不需要再画云气,即能表现出中国山水画中涌动着的生命精神。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欧洲传统静物画的方式去审视刘丹的山石系列。静物画在17世纪开始流行,最富有思想意味的莫过于其中的虚空静物画,艺术家通过骷髅头、燃烧的蜡烛、枯萎的花草等寓意着生命的短暂。刘丹在这块承接了天地之精气的石头中,更向观者揭示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

▲ 刘丹,《小孤山馆藏英石》,纸本水墨,70x175cm,2021
此次展览中,刘丹描绘了明代时期雅好收藏奇石的大家米万钟收藏的两块石头,黑灵璧石和英石。关于石的收藏与鉴赏,宋代有杜绾《云林石谱米,明代有万钟的小孤山馆林有麟《素园石谱》、文震亨《长物志水石》等。而米万钟邀请友人吴彬描绘的《十面灵璧图》长卷,在2020年更是以加佣金超过5亿人民币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排出,使之成果全球最贵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丹描绘的小孤山馆藏石的这两件画作,有着向米万钟和吴彬为代表的中国文人世界、美学理想致敬的意味。刘丹不仅延续了吴彬的画法,还追摹米万钟的眼睛,他用小楷在石的右侧题写前人赏石的文章,将观看和感知融为一体的作为跋文,形成图文并茂的视觉关系。这种堪被称之为“博物学”的视觉形式,事实上在19世纪摄影术发明之前,在中西方广泛流传。可以说,刘丹在用摄影的方式观看和作画,不同的是,呈现在画面上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他凝视石头的抽象感知,此时的观看已经深入到石的内里。对于刘丹而言,这种凝视和描摹,与中国宋代理学“格物致知”的观念,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开篇谈到“穷神变测幽微”的思想相契合。通过这两块小孤山馆的藏石,刘丹触摸到中国古代文人世界所共享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桃源胜境,这也是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遥想,也隐喻着对今天中国文化生活愿景的寄望。我们可以说刘丹是一位古典主义者,无论是他的画法还是他所致敬的那个抽象的古代文人世界。就像在他的创作中,我们既可以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写实画法中看到清晰的线索,也能在中国古代书画系统中不断找到新的回响,这都为其进入世界艺术史,进入世界艺术史互动和交流的脉络,提供了多个通道。而另外一位好古者邵帆,则是通过老兔和老猿的形象,进入到一个超越中国文化情境的荒原时代。如果说刘丹在绘画中呈现出的是一位贬低肉身的禁欲主义者,那么邵帆的艺术中则更看重游刃于青冥与大地之间的肉身形象。

▲ 刘丹,《小孤山馆藏黑灵璧》,纸本水墨,70x175cm,2021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邵帆都是一位结构和解构主义者,他的艺术语言和思想都力图重建生命的形式。这种思想的源头显然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启发,他将中国明式家具拆解,用现代材料置换,形成一种带有强烈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艺术形式。而老猿和老兔的形象,则是他近年来更深入挖掘的绘画主题。较容易理解的是,老猿的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被视为隐逸者的存在,往往作者通过对深山中老猿的叫声,描述一种“悲戚”“悲愁”的情感基调,在《九歌》中有“猿啾啾兮又夜鸣”,六朝时期,猿声与哀、悲、寒、孤、夜、泪、清等视觉意象相关,在唐代的诗歌中,则用冥、霜、晓、旧、惊、啼、穷、愁等语汇描述猿和猿声。通过回顾这样一个文化史的语境,我们在邵帆关于老猿的绘画中,就能清晰地看到他的一种生命意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今天我们皆生活在由石室森林和汽车玻璃窗构建的便捷的城市空间中,已经远离了老猿的悲啼之声,或者,即使我们想回到一片未经开发的荒芜之地,也未必能找寻到猿,亦难听得猿声,更不要说老猿。在这里,邵帆描绘的老猿的形象,也就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老猿被捕捉和豢养在动物园,成为被观看的动物,或者被驱逐至更深远处,以至于使我们完全失去了古代文学中富有的想象力。相较而言,邵帆描绘的兔子的形象令观者难以理解。

▲ 邵帆,《似山非石》,纸本水墨,200 x 235 cm,2017
此次展览中,邵帆展示了多只老兔的形象,远不同于其早期用油彩描绘的萌兔的形象,较为接近近年来创作的老猿形象的系列绘画。兔子的形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也很多,多藏匿在山石、草木之下,并辅之以四时之景。群兔的形象虽然会被技艺高超的画家进行拟人化的表现,但兔子的形象与人形相距甚远,不像老猿与人形非常接近,以至于兔子完全不会被描绘成隐逸的老者。关于为何画兔,邵帆认为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绘画的过程和体验,这就与刘丹的绘画意识有了直接的关联。邵帆在画兔的过程中,便直接感受到一种生命状态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是通过无数的线汇集而出。邵帆并没有像李华生等艺术家用“无形”来指代那个“大象”,而是用老猿和老兔直接指认,如果不是老猿和老兔亦无妨碍。我们在邵帆的绘画中还能看到从来没有可能看过的形象,老兔的唇须,已经化作仙山的石草,而紧闭的嘴则成为幽谷的裂缝,这都使观者不断回到老猿,回到邵帆关于仙人的想象。面对“以兔之名”系列,邵帆像刘丹那样同样描绘了眩晕,观者的视线在跟随邵帆的描线向画面深处延伸时,最终都会进入一个图像的漩涡,这不禁令人想起西方的欧普绘画。同时,我们在邵帆的画作中还能看到宗教绘画中才有的背光,这无不将老兔的形象指向老猿,指向邵帆心心念念的仙界。有意思的是,老猿是被贬谪的仙人,与之相对应的仙鹤是可以飞升的,而老猿则只能被遗留在人间悲啼,老兔的形象也莫不如此,这样,就是邵帆的“以兔之名”系列更多了一层自我指涉的隐喻,就像在很多古代画作中那样,兔子总是躲闪的姿态,鹰不仅在画面之中,也在画面之外。邵帆和刘丹的绘画中都隐藏着第二世界——无论是深山幽谷中仙人的肉身,还是世俗文人世界的精神桃花源——徐累则是通过图像的折叠、并置,将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将不同物质形态,同时呈现在观者面前,构成视觉意义上的重构与再造。

▲ 邵帆,《兔位》,纸本水墨,225x175cm,2018
徐累同样也画石头,只是他没有像刘丹那样将石头置于桌面上凝视,他的绘画更具追求想象力,他将石头(陨石)幻化(晕染)成霓虹的形状,形成一座拱桥。与刘丹追求格物致知的理学精神的石头相较,徐累的“霓石”是一种浪漫的形态、逍遥游的形态、自在的形态。虽然徐累认为“霓石”是他一个时期关于艺术语言与观念思考的重要成果,但并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太多关注,主要还是在于“霓石”传达的信息太过于清晰和明确,以至于研究者并不能对此提出新的解读空间。对于中国绘画史而言,徐累的“霓石”是一种悬置的形态,我们同样只能在吴彬《十面灵璧图》中找寻其生成的源头。相较于“霓石”的漂浮,徐累的“浮石”则与中国艺术史的联系更为紧密,我们会联想到秦汉时期以来的蓬莱仙岛的意象,尤其是在汉代器物博山炉上,仙山坐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意味着只有经过重重艰难险阻的考验,修道者才可能到达。徐累的“浮石”更接近于一块浮石本身,而幽谧的蓝色又使人联想到冰冷的冰山和海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片荒野。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新世纪之初展望在公海实施的“漂浮计划”:假山石成为一位流浪者,在公海中被投下,它的命运是未知与不确定。同样,徐累也将中国传统文人世界中的假山石(关于假山和真山、桃花源和园林的关系,将又是一个意味隽永的话题)放入到杉本博斯的海景中,在视觉上同样创作了一种未知和悬置的形态。以至于观者在面对徐累的绘画时,经常会被其多重的艺术史经验折服,他在画面中制造的重叠翻滚的视觉意象,像是涌动的激流,同样制造着视觉的漩涡,也使观看变得复杂、多变,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诗意或者是其它。

▲ 徐累,《霓石》,绢本,153 x 266 cm,2015年
很长的时间里,面对徐累的霓石、浮石,研究者多是以超现实主义笼统的指代,但这只能说是纯视觉层面的归纳,而其图像生成的基本,乃是叠置,这和西方当代艺术史上的拼贴手法是相近的,与艺术史上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是息息相关的。徐累还有一种绘画极其受到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的影响,像巫鸿关于屏风、纪念碑性的研究,使他注意到了图像内部更为复杂的构造。尤其是对屏风、屏障,引导着徐累的绘画走向视觉空间的深处。这种视觉形式与徐累对褶皱的概念的关注也是极为相关的,这就使研究者不得不注意到学界近年来的德勒兹热。当然,徐累作为一位视觉艺术家,他更关注其画面最终视觉层面的合理性,至于准确表达一个怎样的含义,则非其必然要思考的内容,这种模糊或者是开放的解读方式,或者是所有观者面对其绘画所津津乐道的。徐累在画面上导演了一出出神秘戏剧,画面就像是空间深处的一扇门、一扇屏,在暮色降临之际,这场神秘的戏剧都会自行上演,而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时空瞬间凝固。

▲ 徐累,《浮石》,绢本,152x260cm,2015
最后,尽管我们在刘丹、邵帆和徐累的绘画中看到中国绘画史的图像和思想经验,但不能忘记的是,如果没有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现代水墨实践和探索,是不可能在今天有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不断出走并不断回归的自然形态。这三位艺术家有着不同的生活、思想、知识和生命经验,他们最终想要解决的还是艺术史和思想史都要面对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走向生命的自由,让一切坚固的挂碍都消逝不见。就像他们都在收藏古物,中国古代文人世界传递的这些物象中,寄寓着那个理想精神生活的魂。毋庸置疑的是,民族和国家的身份意识潜在于三位艺术家的文化意识中,他们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立足艺术史的那个点,这是一个中西方文化和历史交汇融通新的时空。就像是这个展览的“极地清晨”,三位艺术家都像是隐居于荒原者,那么,艺术创作是要精心营造一座绝美的私家园林(桃花源),还是要离开极地?这将是三位艺术家要继续思考的命题。
魏祥奇,美术学博士,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从事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和写作,在中国美术馆及海外执行策划了多个重要展览项目,近年来尤其是关注198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艺术的研究,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参与了“青衿计划”、“新朦胧主义”等系列项目的策划工作等;同时专注于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