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艺术之于社会的关系在今天不断被讨论,如今诸如社会性艺术,参与式艺术,对话艺术,社区艺术、社会介入性艺术等词不绝于耳。其特点则体现在艺术家、作品、参与者、以及相关社会运行机制几个维度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上。这也涉及到艺术生产方式的更新和对艺术理解的新形态。本次专题推送我们将以实践形态和地域为划分,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这些实践是如何重构今天我们对于艺术及其行动的认知和理解的。 |
本文共6494字,阅读大约需要17分钟

艺术家安置团体(APG)
“艺术家安置团体(Artist Placement Group,简称APG)”是由芭芭拉·斯蒂夫尼(Barbara Steveni)和她的丈夫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于20世纪60年代共同创立的,最早出现在伦敦。后陆续有其他艺术家加入并一直活跃至80年代中期,其中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创始成员有巴里·弗拉纳根(Barry Flanagan)、大卫·霍尔(David Hall)、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安娜·雷德利(Anna Ridley)和杰弗里·肖(Jeffrey Shaw)。

芭芭拉·斯蒂夫尼(Barbara Steveni)
这一组织的成立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艺术家是一种未被社会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艺术家们被画廊系统隔绝于公众之外,在艺术世界里,他们也被隔绝于工业、商业和政府的世俗现实之外。而APG的想法是,让艺术家们带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影响他们所在的组织,并产生积极效应。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让艺术家们融入工业和政府机构,通过进入权力的生产环节参与决策,在意识层面改变在机构里工作的工人,而不是直接帮助他们。艺术的功能转向“决策”,艺术作品转变为计划或项目。该组织一直积极寻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定位艺术家角色的方式。同时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概念艺术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的是APG既不是艺术家团体,也不是职业介绍所。没有明确的成员,而是一个松散的艺术家网络,他们被建议安置。除了创始成员,还有许多艺术家也在不同时期加入了APG,如Ian Breakwell(伊恩·布里克韦尔)、Stuart Brisley(斯图尔特·布莱斯利)、Hugh Davies(休·戴维斯)、Andrew Dipper()、Garth Evans(加斯·埃文斯)、Leonard Hessing、George Levantis(乔治·莱万提斯)、Ian McDonald Munro(伊恩·麦克唐纳·门罗)、David Hall(戴维·霍尔)、Marie Yates(玛丽·耶茨)、Rolf Sachsse和RosSachsse- schadt(罗斯·萨克斯·沙特博士),他们中有画家、音乐家、作家、摄影师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来自社会其他领域的成员和支持者。《观察家报》记者彼得·博蒙特称APG是“20世纪60年代最激进的社会实验之一”。[1]

工作中的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
在APG成立的初期,约翰·莱瑟姆就已经是一位知名艺术家了。现在,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那些用书做成的作品:将书摆成一座座高楼,烧掉、将书扔进装满小鱼的鱼缸…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966年进行的行为表演艺术《静止与咀嚼/艺术与文化》(Still and Chew/Art and Culture),这里他和自己的学生咀嚼了一本从圣马丁艺术学院图书馆借来的格林伯格的《艺术与文化》,然后将这些咀嚼过的碎屑装进一个瓶子里,并且贴上了“格林伯格的本质”的标签,而他本人因为这次破坏行为丢了饭碗。在同一年,他再次公开冒犯了现代主义——他们创立了APG。而这个想法的雏形产生于斯蒂夫尼,1965年的一天晚上,当时她正在为激浪派艺术家Robert Filliou和Daniel Spoerri在西伦敦郊外的工业综合艺术工程(Slough Trading Estate)搜集碎石。在这过程中她觉得,如果艺术家直接在这些工厂中工作,而不是采用工厂外面那些废弃的石头,那样他们的作品也许将发挥更大的社会性作用。而莱瑟姆也意识到,斯蒂夫尼的这个想法和自己的时间性“事件结构”不谋而合。第二年,他们组成了理事会——艺术家安置团体就此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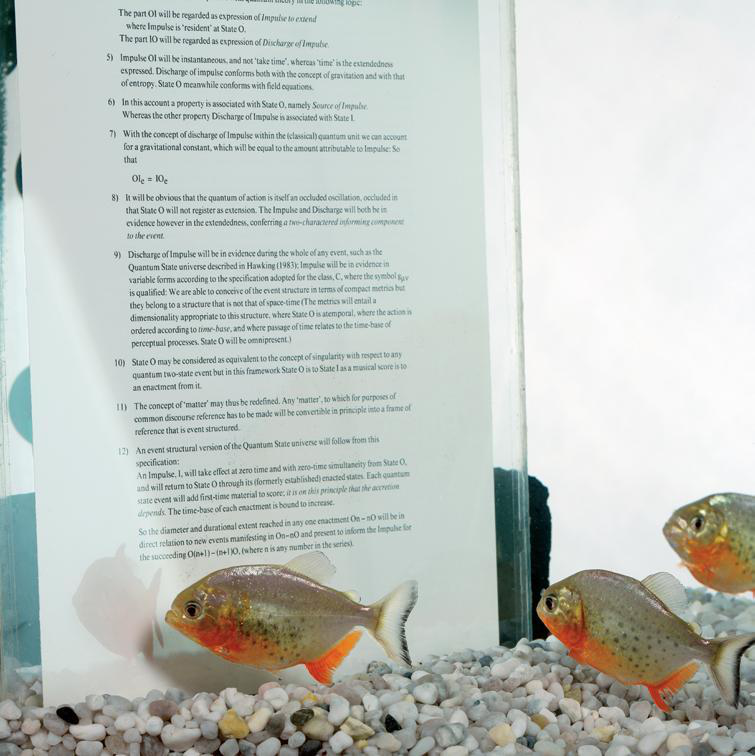
John Latham,《他们学得很快》,1988,鱼缸、南美小鱼、书页
刚开始APG经历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时期,它由一个艺术家组成的机构,后来转变为一家有限公司(APG Research Ltd.),董事会也由工业(为艺术家提供创作材料、赞助或安置场所等)、媒体、一些公会和艺术机构的代表组成,斯蒂夫尼是与这数百家公司和组织,以及潜在赞助商和提倡者建立联系和保持通信的主要驱动力。到了1969年,这个组织迎来了第一批安置计划。他们所要安置的这些艺术家包括Stuart Brisley、Barry Flanagan和David Hall。因为APG开始时会员寥寥无几,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部分艺术家都与莱瑟姆有个人交情,或者是通过艺术学院和讨论会认识的。将这些艺术家联系起来的是:这些艺术家没人搞架上绘画,而且都乐于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中,并且都喜欢事件。而早期的APG安置几乎完全是与行业合作伙伴协商的。这与美国和德国工业联盟的“艺术与技术实验”(EAT)项目和“工业领域艺术家”(Ars Viva)项目则倾向于技术合作和为艺术家提供工业材料不同,APG的做法远不止于此。

英国钢铁公司,Garth Evans的作品,照片:Malte Ludwigs
APG对赞助和赞助模式并不感兴趣。斯蒂夫尼规划出了安置计划的基本程序。她通常是这样做的:给那些有可能提供赞助的机构写信,陈述APG的宗旨,然后让这些机构支付艺术家一定的费用(通常为2000-3000英镑),这位艺术家就会来到该机构所在地工作。她建议接收艺术家的机构把他/她当作一位具有创造力的外来人来到了他们中间,按照APG的术语,就是一个业余的“意外来客”(Incidental Person),只不过被贴上了具有浪漫色彩的“艺术家”标签。斯蒂夫尼将APG基于新的赞助形式,是为了在艺术家和那些工作人员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他们之间能够彼此交换视角。而她所计划的最理想的安置程序有三个步骤:首先,要经过几个月的“可行性研究”,考察安置的可行性,,在此期间,艺术家们要熟悉具体的环境,为接下来更长的安置制定一个艺术建议。然后就实际问题和法律问题与目标机构达成协议,最后进行方案的展示。从档案上来看,早期的参加组织多为商业和国有公司,例如英国铁路公司和英国钢铁公司。[1]

加思·埃文斯,《分解钢铁》,1971年出版,1969年由APG/英国钢铁公司奖学金资助。
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APG代表艺术家与行业和政府协商了大约20次安置,除了探索艺术及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还主张艺术家应当走出自己的工作室,走出美术馆及画廊,走入正在进行的情境中。与其他驻留项目强调作品及展览不同的是,APG更强调这个过程中如何展开讨论和打开思维。他们认为APG的目标不是让艺术家为行业或政府服务,而是让他们在工作室和艺术市场之外的特定环境下(一般是被视为和创造性思维格格不入的环境中),采取行动,研究工作项目和实现艺术作品,正如APG的格言所说,“环境是成功的一半”。而进行安置的理由是,艺术家在安置环境中的存在对于安置的组织和艺术家是互利的,艺术实践和知识将不在局限于工作室和画廊,他们的活动领域将扩展到商业、工业和行政领域,是让艺术家进入权力中心的环境并且和从管理层到劳动阶层的各个阶层员工相互交流。

David Hall,《天空》系列之一,后并入《Timecheck》16mm彩色电影,45分钟,艺术家被安置到British European Airways(伦敦)时所做 1969-71

乔治·勒万提斯(George Levantis),海洋舰队有限公司,1975年©乔治·勒万提斯。
APT的创始人,艺术家和合作人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改变社会对艺术家的看法,但是这种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组织安置的结果有时候促成了一部电影,或者一座雕像,但这并不是斯蒂夫尼和莱瑟姆的最后目的。他们一直致力于改造社会,但在这过程出现了许多问题。
1、首先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组织为什么要进行安置?人们总是对进行安置的目的产生误解,而遭到误解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安置项目具有对抗性(安置大多是在商业,工业和行政领域的内部管理层,而这种安置在某些方面,艺术家或多或少会与原本在内部的人员产生利益或思想的冲突),而APT往往是在两种相对抗的力量之间形成永久,却不稳定的张力。正如斯蒂夫尼一再强调的那样,这个组织的宗旨并不在于通过艺术家固有的创造力和他们对于商业规则的相对忽略来将工业进行人格化。就算承认APG对于批判立场和商业之间的调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做法,然而,按照艺术家Ian Breakwell(伊恩·布里克韦尔)的说法,最有效的安置也不免发生“不悦的争论”。Breakwell被安置在健康与社保部,他的职责就是在精神病医院和专业人员一同工作以改善那里的环境。他被雇为专业观察员。专业人员利用他的“日记”来引入一种更具有咨询性的方式。但是后来他要求病人谈谈自己对于这所监狱式的医院的看法。结果触怒了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认为,这个艺术家已经越权。研究最终被《公务员保密法》所限制。但是,Breakwell所在的专家组却对他的安置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日记”应该被作为“一个真实持久,并且(在Breakwell看来)关于精神病的精神病图像”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这也正是APG希望达到的结果,但对于这个结果,任何思想开放的组织机构都要重新思考他们的领导组织和基本的出发点。APG的意图不是要惹事生非、挑拨离间,而是希望改变这些机构中工作人员的认识。

1978年对疗养院的采访©Carmel Sammons
2、其次问题是在这一系列的安置过程中,有些艺术家已经被体系化了(是由于接触的人与事不同,观念产生了变化,或者受困于经济条件限制亦或者是被利益所驱使等,在安置的环境中被同化,成为政治或工业等体系中的一员)这是在所难免的,从他们自己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有的人选择了在基层工作,有的选择了在管理层工作,他们在安置的过程中就已经变得体系化了。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该组织内部的分歧。例如1970年被安置在Hille家具公司的艺术家Brisley,他选择了在工厂工作,这也给APG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在他的艺术项目中,他问工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应该得到怎样的改善,并且相应地实现了一些小的改善,例如用工人们喜欢的球队制服颜色涂他们使用的机器,并且引入了移动留言板制度。最后,他的安置计划落实到了一座由212把椅子连在一起构成的雕塑上,Brisley觉得,他的艺术家身份已经在这个项目中开始被模糊了,他介入了劳动阶层,这也将他从艺术中移开,让他更加地接近了一种“集体情境”,他不得不承认“工厂和管理阶层”之间的“永久性矛盾”。他最终认为,APG已经沉醉于管理而不能自拔,这个组织的结构变成了“一种组织严密、高度专制的家庭经济,”并要求成员对其忠贞不二。所以他离开了APG。[2]

布利斯利在希尔家具公司正在制作他用罗宾椅搭建的装置 1970
3、APG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集体,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公开展示往往是表演性质的。在杜塞尔多夫美术馆(Kunsthalle Dusseldorf, 1971年)和伦敦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 1971/1972年)举办的6场展览期间,APG的临时“办公室”尤其体现了他们在表现和真正谈判之间的矛盾心理。APG的艺术家们聚集在一个被称为“雕塑”的中央谈判桌旁,与来自商界和政府的受邀代表讨论APG的目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和机构世界的语言和美学在APG的风格中清晰可见。但也正是这些展览APG开始受到了大量的抨击。

艺术家安置团体的互动讨论展区“雕塑”现场,在“艺术与经济”展览上 1971
海沃德画廊的展览结束后,彼得·富勒(Peter Fuller)、古斯塔夫·梅泽尔(Gustav Metzger)和斯图尔特·布里斯利(Stuart Brisley)等马克思主义批评人士(与该组织本身关系密切)指责该组织追求改革,却忽视了真正的阶级冲突。这些类别在APG,尤其是莱瑟姆的头脑中几乎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艺术家占据着商业和政治利益之外的第三个位置。
Guy Brett在伦敦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这个展览给人以会议室的感觉,仿佛里面正在进行高层会务。”
英国《卫报》的Caroline Tisdall在观看了Dipper的档案之后也说:“这些视觉材料和公司的宣传品看起来别无二致。”(这些评论家表达的官僚气氛——Benjamin H.D. Buchloh后来(对于观念艺术而言)称之为“行政美学”)。各种各样的机构特征引起了焦虑,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艺术与更高级的管理机构进行合作或向其臣服妥协。

“艺术与经济”展览现场 1971
艺术家Gustav Metzger在《国际工作室》(Studio International)中所说,他认为,APG试图寻找一个“中间立场”,因为“20世纪的历史表明,这样一种中间立场总是导向了右倾。”他对这种倾向嗤之以鼻。
最猛烈的批判还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批评家Peter Fuller, 他在1971年《艺术与艺术家》(Art and Artists)杂志的专栏里讽刺了莱瑟姆和斯蒂夫尼的不成熟,笑话莱瑟姆对于马克思一无所知,还不以为然,并且还讽刺地引用了斯蒂夫尼的原话:“谁是托洛茨基”。Fuller认为,商业与艺术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对后者极为不利了,因此,使得APG的安置变得失去了批判性,如果APG对此还没有任何意识,那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他发现:“要想改造资本主义,并且提出一种非商业性的,或者‘利益驱使’的价值结构,那么至少需要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小组讨论:“在政府和行政任务中运用艺术潜能”,库恩斯特维雷恩·波恩,1977年©波恩市档案馆,摄影收藏-弗里兹·费舍尔
就在此时政府撤销了APG的公共资金,这让组织雪上加霜,而对于撤销的原因,一位官员说,这个组织不“直接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关心“社会事业。”
但这些并没有摧毁APG的信念。为了改善对于机构的公共投资,APG最终还是采用了它避之不及的统计方式,而且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统计数据的分析将艺术对于社会的贡献进行了量化(观众人口构成、市场营销和参观人数等)。可以说,APG率先对艺术家采取了管理顾问的机制,这也预示了艺术商业化趋势的来临,也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后来APG重新评估艺术家作为“意外来客”的角色,在海沃德展览短暂中断后,APG于1973年进行了改革,并开始进入政界,在政府部门中安插人员,希望能够渗透到国家政治机器的核心,它在《Time Out London》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称“从短期项目到长期协会,各种组织中的艺术家都有很多可能性”。

Roger Coward,环境部,1975年©Roger Coward
可是这个集体政治野心的增强,导致了一系列的分歧,APG所有的活动停止了三年,后来被重新命名为“O+I”或者“机构与想象”在1989年重新出现,但他对艺术家在行业中的角色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继续推动跨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学科项目。2004年,伦敦泰特美术馆购买了APG档案。不久之后,联合创始人约翰·莱瑟姆于2006年去世。2012年,伦敦雷文罗画廊(Raven Row Gallery)回顾了APG的早期作品,举办了一场大型回顾展,其中包括一些作品的展示,以及泰特美术馆借出的相关文献。2015年在柏林Kreuzberg/Bethanien美术馆举办了进一步的回顾展,为2016年在爱丁堡夏厅举办的进一步展览奠定了基础。


2015年在柏林Kreuzberg/Bethanien美术馆展览现场
从今天看来,APG的贡献在于:它试图找到一种非工作室的艺术生产方式、为长期的、深度跨学科的研究创造机会,重新思考展览的作用和我们的评价标准,它使艺术的价值不再困于可证明的参数和经济效应。并且它还强调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艺术的价值。对于近来有关社会性艺术的探讨,特别是关于艺术活动的评价问题,APG的贡献更加突出。就算APG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也预示了社会的变化。尽管这些成就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呼声。[3]
另外,APG对于社会性艺术的策划方式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在“Inno70”展览之后,APG不再采用展览的模式,而是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展现其项目。这也构成了作为“话语平台”的展览,以及作为呈现过程性(而非物品性)参与艺术的研讨会的基础。

APG成员在卡塞尔文献展,德国,1977年。从左至右:伊恩·波克韦尔(Ian Breakwell)、芭芭拉·斯蒂夫尼(Barbara Steveni)、尼古拉斯·特瑟芬(Nicholas t史蒂芬)、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和休·戴维斯(Hugh Davies)。
APG自从70年代以来,在观念上这个组织促进了更广意义上艺术与经济的变革。
近年来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APG的成果,这种历史性的重新评价是在年轻一代的策展人、雕塑家和艺术家的作用下得以实现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艺术实践应该和APG的活动相仿。另外,重新评价之所以得以实现还与莱瑟姆的去世(2006)以及泰特博物馆收藏的这个组织的档案的公布有关。现在看来,APG的活动显然构成了当前关于艺术的功能性和社会性争论的核心。为了勾勒那些将社会性过程想象为艺术的当代历史——通过艺术达到社会变革的前卫梦想,因此,更需要回顾一下莱瑟姆与斯蒂夫尼的卓尔不凡却又争论颇多事业。在我看来APG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跨学科创造的可能性、艺术家驻地活动的经验和改变对艺术的固有观念与通过艺术为媒介对社会进行创新性变革(类似于文艺复兴)的可能。所以尽管APG的理论矛盾重重,其内部争论不休,但APG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
参考资料:
部分内容与来源于维基百科
部分来源与ARTFORUM艺术论坛
[1]基础资料来源:https://www.tate.org.uk。
[2]资料来源:https://en.contextishalfthework.net。
[3]http://www.frieze.com/issue/article/context_is_half_the_work/
参考网站:https://contextishalfthework.net/archiv-ausstellung/barbara-steveni/
部分文献译自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在艺术论坛发表的文章,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艺术史副教授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