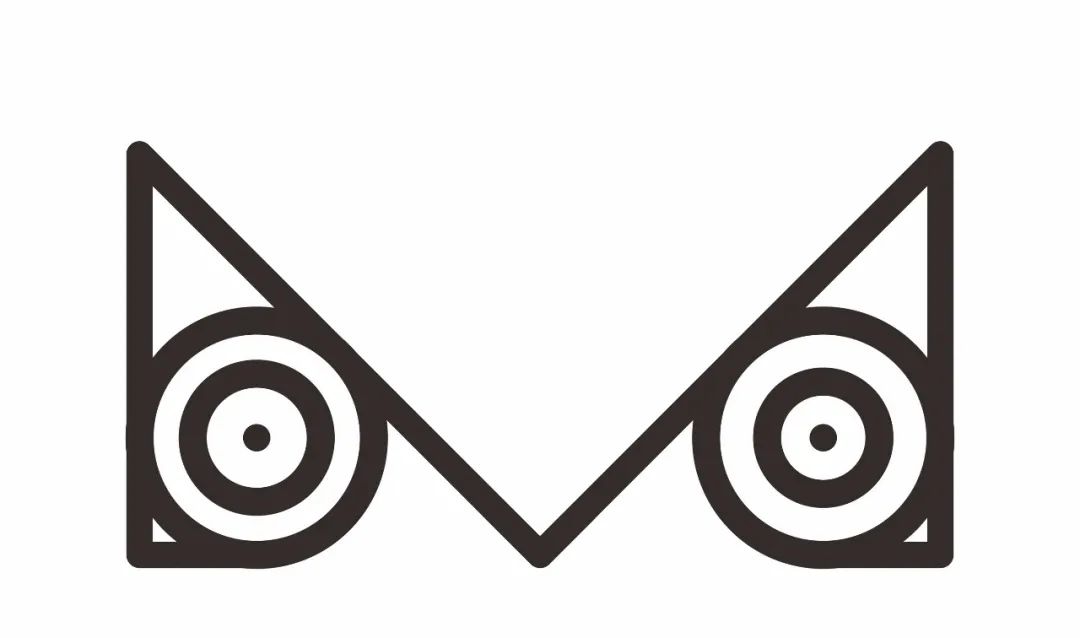
X
口述当代艺术06
理想,我已经在做了
口述:徐薇
记录整理:楚思贤
在过程中生成
你问我,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要如何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去推进现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现在已经在做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需要所谓的一个亿或者外部的巨大资源。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想要做自己的事情,跟有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太大关系。就像你和我都有这样的经验,都是从自己发声开始,对不对?
只要你清晰自己的价值观,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连接你。这些事情需要成本吗?成本就是我们的认知和曾经的一些积累。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按部就班地持续推进。这些事情跟一个亿或几个亿没有太大关系。当你真的有这个钱时,未必有自己去亲身实践的耐心,可能会安排很多工具和人手去实现,但这样反而可能会丧失我们在实际过程中生成的一种真实的东西。我觉得生成和设计是两件事情。特别是在艺术的维度,或者任何维度。你以为的设计,最后往往是无效的。很多时候,你只有在真实的体验中,才知道下一步自然该怎么走。而这种体验往往是在某种匮乏感的逼迫下才能实现。
所以,我认同你提出的“过程性转向”。以为“过程性”意味着你首先要彻底放弃目的性,而是为了过程本身。让体验成为一种驱动力,再进入下一个过程中的体验。这是一种我认同的生命方式,不只是创作方式。你隐隐约约知道大概要去向哪里。比如你我的驱动力,可能都是来自与对真实的某种执念。可能为了澄清一些你认为有问题的东西,才会一定要去表态。
另外你提到这个问题,实际是“资源”的匮乏感和“理想”的遥远感,让我想到看到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TA是一个艺二代。内容是如果有财富自由,就去报最想读的专业,去遥远的国度做和艺术无关的事情,这才是TA真实想过的生活。我的第一反应是,你的父母也并没有要求你挣钱,只希望你能做好自己。那到底是什么在障碍你?只因为没有钱吗?也许很多时候障碍我们的只是自己的执念。这个执念恰恰是社会规训给我们的成功学设定的。似乎只有像马斯克、扎克伯格那样成功才能实现梦想,可我并不这样认为。
很多年轻创作者和我说现在创作养不活自己,先去挣点钱,有底气了再搞创作。大多人都在这样选择,“既要、又要”的生活在逻辑上成立,但在操作中往往两边都做不好。乔治.奥维尔曾建议创作者如果要兼职也不能从事“半创作性”的工作,要无比珍惜创作上的完整精力。我知道真正的创作每次推进一点点都非常艰难。如果你选择的赚钱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还拿什么东西往前推进创作?
我不觉得现实中的资源匮乏是阻挡做事的真正阻碍。反而限制可以逼迫你只用自己的力量,尽量充分地表达观点,往前推进,这是重要的。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不觉得现在做的事情与需要的资源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要调动资源,就是希望自己生活更自律,对时间的利用更勤奋。比如说人生只有几十年,在老年之前的时间里,让工作效率更高一些。
我已经在做想做的事情,一切就会自然生成。在现在的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被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影响力还是你要连接的人或资源,大家是因为认同观点来联系你,而不是奔着你的钱来的。如果奔着你的大平台来的,也不是真正有用的人,连接到的资源也不是真正有效的资源。
我的工作是“澄清”
我一直觉得我做的是“澄清”的工作,而不是构建。无论是写文章、做视频,还是办展览,我只是想把一些大家本应知道的事实和真相呈现出来。因为很多真相往往因为没有以当前推崇的方式展示,所以被忽略。比如说现在很多画廊推崇那些平滑、精致的艺术,很多不懂艺术的人只会看到市场推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好的。
所以,我做的工作就是澄清。我想把一些真正有价值但没有被市场推崇的作品、观念和价值观介绍给大家。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解读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感知不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容易被遮蔽,因为它们往往不是以吸引人的感官为目的。真正价值的呈现常常是一种深入内部的方向,但这种方向在感官喧嚣的时代,注定不容易被人看见、理解或相信。
我的工作就是澄清,因为不能让艺术家自己说。这是有问题的。在我接触的经历里,我看到太会说的艺术家往往作品并不匹配。这是一个悖论。你知道吗?“说得好,做得好”这种标准我觉得是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规训。在西方上课都要做presentation,训练你的某种展示能力。是的,帮助别人更好理解你是一种必要的沟通能力,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必要能力。艺术家最重要的能力还是创作本身。真正好的创作会散发出不言自明的东西,如果你能在这个基础上稍微说几句也可以,但不要让解说的力度遮蔽了作品。
我本能地不喜欢太能说会道的艺术家,会本能地产生警惕。这是骗不了人的。把一些东西逻辑化或表演化,是一个重要的沟通能力,便于别人理解。但这与实际的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逻辑思维进入的是设计层面,是一种理性思维,但这种思维过于强大时,不能造就好的艺术创作。
艺术写作和艺术软文
我以前是文字工作者,工作时拼命地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写的东西必须要有逻辑,有层次,层层推进。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长期训练后,我开始真正进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纯创作性的写作让我碰到了一个瓶颈。我会发现自己永远放不下观众,脑子里永远有一个读者。我总想着怎样才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诠释自己的作品,这让我极其痛苦。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让自己从这种惯性中挣脱出来。但我并不是说放弃了表达清晰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内化在我的心中,只是不会再是条件反射般的服务式自觉。因为我已经真正知道自己要推进什么,澄清什么,那个“真相”吸引着我,这时就不再那么需要观众的鼓掌,只需要往前走。
时代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不同的人。现在,要生存下去确实很艰难。你不仅需要巨大的屏蔽能力,还要拥有丰富的综合素质。这确实难,但我觉得挺好。
不管我推崇的方向还是更青睐的风格,它们都是容易被遮蔽的。因此,我希望从内心保护它们的纯粹性。不希望它们迅速融合当下的语境。在某个点上做到极致的纯粹性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在某个维度上有一个纯粹的突破,已经值得我们去看见和认可。
比为什么现在艺术家“会说”的综合素质如此重要。我觉得这种反向逼迫还是来自于市场,它不鼓励,也无法看到那些仅靠作品本身成功的艺术家。如说谢德庆,他的作品本身就有极大的震撼力,即使不了解他的人,也会被他作品的内容打动。这种程度的震撼和艺术家的个人能力无关,而是作品本身的力量。
那么现在,如果没有创意说明,我们就无法判断作品的好坏吗?我当然是希望有一天大家不需要说明也能感受到作品的好坏。当然,这可能有些理想化。从不懂到懂的过程需要我们这些工作者去推动,而不是永远喂他们奶。如果一个艺术家也永远需要用创意说明来解释作品,说明这个工作本质上是无效的。
最终,市场的正向发展,一定需要整体美育和国民美学鉴赏能力的提升。目前大多数的艺术推广还停留在软文层面,并没有构建观众和市场认知的升级。这种合法性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合法。它既没有追根溯源找到历史背景,也没有结合当下人的心理需求,让观众通过共鸣感受到合理性和必要性。很多时候,只是从哲学里拿一点,从谱系里拿一点,拼凑在一起,形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无效的,也导致了观众永远需要一个有知识的人为他们解说展览,写文字装点门面,好像这样看起来就合理了。对吧,然后大家都在做无效的工作。
看见被遮蔽的面
我一直在说工作的有效性,所以一开始会问你,你想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啥。大家先把目的搞清楚,然后奔着这个目的去,所谓不忘初心。我做的是澄清的工作。澄清之后,你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看到的,哪些东西虽然摆在眼前,但也可以选择不看。我希望建立观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天他们可以不需要我们去帮他们说明也能理解和感受。但这可能太理想化了。
首先要让一些重要的东西被人看见。我现在唯一能推进的方式是通过自己发声,让认同我的人来找到我。我发现去找别人是无效的。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你想跟他们说你的观点,主动去找他们是无效的。只能坐等,但我能等来是因为我持续发声。我唯一等那些人来找我的方式就是持续把我的观点说清楚,以我力所能及的方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先剥离那些过于感官浅薄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够了。现在这些塑胶感的东西如此猖獗,说明这个潮流也要退去了。应该是要到一个往内走的阶段开始了。前两天我看的书里写得挺好,是法国前教育部长写的一个哲学小册子。他认为哲学史发展到现在,人们从尼采之后都在解构,消解曾经的权威。权威感来自于宗教性和物质主义,即金钱和权力。作为一个生命体,你要真正深入,要脱离这两者的束缚。那么第三条路在哪里?第三条路隐藏在每个生命“内在的无限性”中。我们推崇的方向都是接近这条路的一个小小的入口,我们都在往这个方向靠近。
就像一个立方体,我们眼睛里最多看到三个面,但还有三个面是看不到的。有些事情在物质世界里看不到,但它们又实实在在存在,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必要性。现在我们都求快求效果,只看到那三个面,但不能说没看到的就不存在。所以我的工作是让大家在看够前三个面后,试图追求那些看不到的面时,给予一些支持和引导。这就是我的工作,因为被遮蔽的面本身就是存在的,不是我创造的。
和当下死磕
虽然我不是宗教人士,但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智慧是值得学习的。就像佛法说“本自具足”,这里的“具足”不是说已经够了,而是指向一种无限,意味着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种充分性没有上限,包括人心的堕落也是没有下限的。人的可怕性在于可以无限地向上或向下发展。
我们至少不要把大家引向那种向下无限的艺术,对不对?在过程性中,建立一种与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关系,而不是脑子里只有过去和未来。这是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她说我们有两种逃避方式:一种是逃往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怀旧型的东西很容易煽情,因为它让你与当下脱离连接,把你带到过去某种安逸或舒适的感官里。其实这也是一种逃避。
还有一种是奔向未来,比如AI和ChatGPT这些,好像未来可以允诺你一个无限光明的希望。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与当下无关,因为当下太痛苦了,无法忍受。
我欣赏你所谓的过程性的提法,因为它必须把你拉到当下,让你无处可逃。你必须认真地与当下对抗,这是真正人的内在力量来源。它不是来自逃避,而是来自于死磕。就像keep的口号“自律让我自由”,也像无限循环的西西弗斯,你必须与自身的重力和周围环境的压力不断对抗。
这是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的路,你要敢于诚实、笨拙地与当下死磕。
坚固之物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坚固的东西。这是我判断人价值观的重要标准。我曾经问过我的朋友,我说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相信有坚固之物的人,一类是不相信坚固之物的人。后来我朋友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反馈,他说其实有三类人,第三类是不确定自己相信不相信的。
所以,你是否相信有些东西是超越金钱与权利的,其实就这么简单。你相信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它的价值大于金钱和权利的价值。比如在人类遇到巨大苦难的时候,比如战争或者几年前上海疫情封控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空前的团结,对精神性的需求空前强烈。当大家都受苦的时候,你会发现再有钱再有权,也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能拯救我们的只有超越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我们无法明确地确定这些东西,但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感知到它,连接到它。
通过这个“坚固之物”这个标准判断很多人的作品和言行,就能明显看出这个人是相信某种东西还是不相信。很多人不断解构,把自己和大家都视为某种虚无,而不是去相信某种可能,把虚无的深渊变成了信仰,但也结结实实地影响很多人,形成了他们的团体。
每个人在持续发声时,都会吸引一群与自己同频的人。因为这些人发自内心地认同这种美学,并能从中获得慰藉。在暴力性发泄中,或者以揭示丑恶的方式呈现丑恶,人们能获得某种慰藉。但这最终可能会让你成为深渊的一部分,什么都变得无价值。
然而,我发现这类虚无的人又很臣服于某种看似权威的表象。比如,有人推崇那些用学术大词表达的人,这种表象能让他们折服。其实,真正的真相不在这种大词的构建之中,而在真实的感官和感觉中。
反思崔灿灿
我通过观察发现,策展人和艺术家一样,他们的代表作完全贯穿了个人气质。比如,我很欣赏崔灿灿早期做的是乡村洗剪吹和夜走黑桥系列,这些作品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和草莽气息,为当时的艺术圈注入了很强的活力。但现在再看他的展览,曾经那种最令人惊喜的,鲜活生猛的东西消退了,我觉得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如何社会成功学的规训下,让自己变得拧巴、痛苦、平庸的过程。
他不断跟大咖艺术家合作,打入主流语境。主流没有问题,但一切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打入主流能更有效的传播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是有意义的,而如果只是写软文,为了自己站在聚光灯中间,有一种成功的幻觉,一旦选择和真实失联,那当初最珍贵的气息就不复存在了,最鲜活的创作力就消退了。
他为什么要推“断裂的一代”?因为他研究85到2000年左右的艺术史后,认为可以通过个人推出一个潮流来定义时代。他也许想复制某种栗宪庭的操作。但事实上,这种推出和真正的时代关系不大,因为不仅是出好作品的时代过去了,而是有效的潮流需要具有批判性的关系,而不是顺流而下的关系。那你说现在策展人能专门策划一个群展来批判艺术家们吗?谁都不会允许这发生的。
栗宪庭说的直觉观察是艺术真的要跟人的生命发生关系,跟时代的个体生命体验和趋向性发生关系。为什么他之前推崇“大灵魂”?因为他认为艺术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代的灵魂。如何通过艺术方式呈现、感知、回应、反思和预警时代的某种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更有某种时代的责任感。而现在的艺术,非常个体化,非常个人的感官化,沉溺化。所以,不仅是黄金时代过去了,具有责任感和悲悯的批评时代也过去了。
但我还是希望更多批评人、策展人能做一些不计代价的事情,去拨乱反正一些可能,毕竟为了挣钱何必进入艺术行业,有太多行业可以选择,既然本身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就要不忘初心,在精力最好的阶段去创作真正的价值。
艺术的感知
其实每个人的路径不同。但是,当你真的能够抛下所有外界的干扰,扎扎实实地去感知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会发现这是一种类似于开悟的过程。不管是艺术的认知,还是对生命的认知,都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在创作过程中,你一下子感觉到了那个关键时刻。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突然意识到,画什么不重要,怎么画才重要。画什么指向的是那个目的,但你不能以目的为导向去判断这幅画的好坏。你需要去除目的,去看它到底是怎么画的。扎扎实实地进入艺术家的每一个笔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里,感知他的生命状态,这样你就能一下子判断出这个人的高低和境界维度。
这种体验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清楚,但我希望听到我描述的人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认知过程,哪怕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对于将来清除干扰会非常重要。为什么大家爱那些浅薄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不好,他们觉得挺好的,觉得挺愉悦的。很多朋友做了很多年藏家了,都觉得挺好的。人会软弱,对于这种好看的诱惑和舒适感的诱惑是很难抵御的。
我一直反对说我非得读个艺术史,读点哲学,然后才能听懂艺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些是辅助你去把东西搞清楚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帮你把这个坐标理得更清晰,辅助你把一些认知构建得更完整,放在一个时代的语境下,从某种时代社会心理去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它是一种辅助工具,但也不能把自己堕入到非本质的知识和信息中去。还会构建出一个自认为自己很懂的假象,但也许从业几十年,对作品本身依然没有感觉,只能靠艺术家的创意说明或有名没名来判断,这样的从业者我见过不少。
如果要做有效的工作,就要相信真实,直击本质,不要浪费生命和时间。
(以上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思考和立场,仅供参考)
受访者介绍

徐薇
生于上海
艺术写作者,独立策展人
著有《艺术的末法时代》
采访者介绍

楚思贤
一个构建当下绘画勇气的工作者
1992年生于泸州
2019年毕业于意大利乌尔比诺美术学院绘画系研究生
视频号/小红书/b站up主:FreemanArt
目前生活工作于四川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