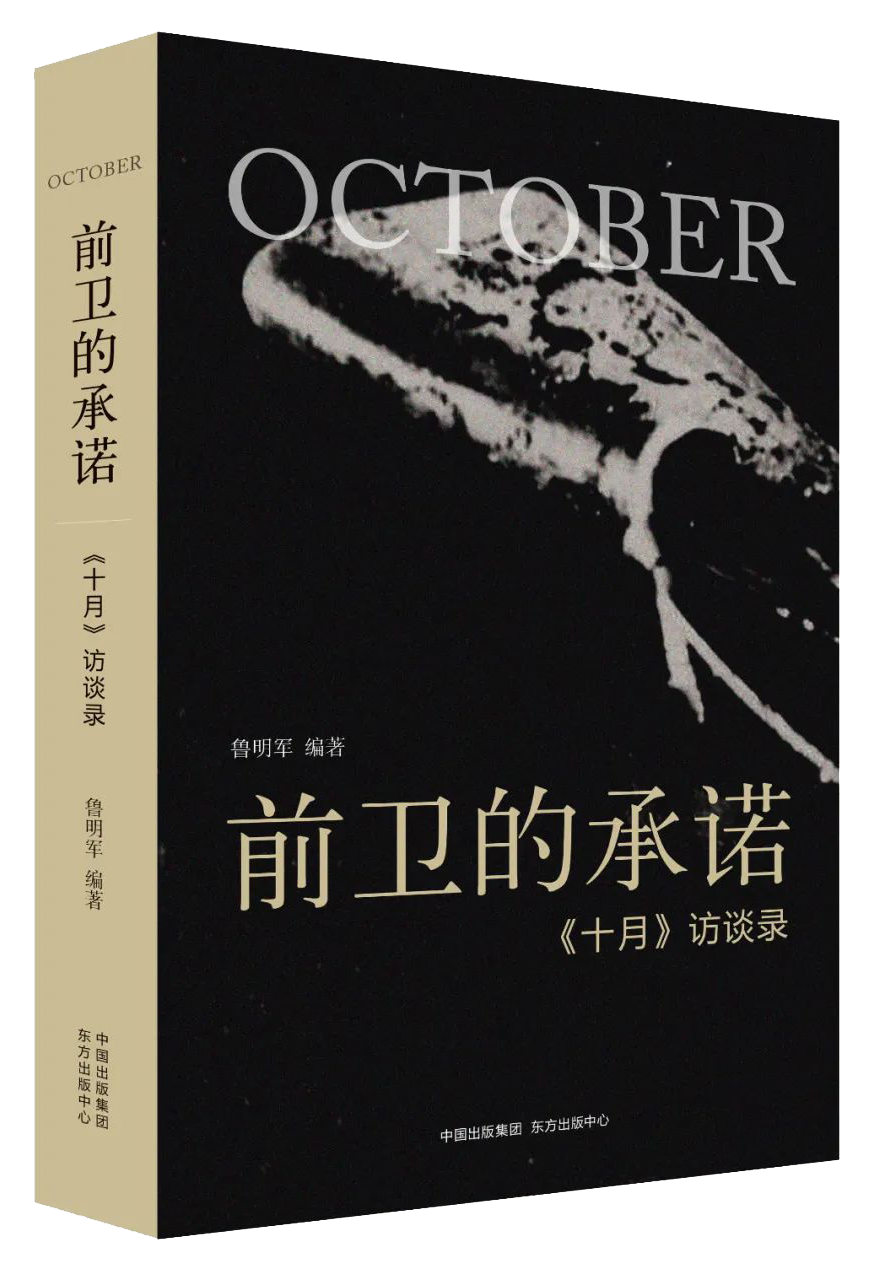
本文摘自《前卫的承诺:<十月>访谈录》一书,
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3月。
《十月》:去政治化的政治
——卡罗琳·A.琼斯访谈录
鲁明军

|
卡罗琳·A.琼斯(1954—),麻省理工学院艺术史系教授。著有《全球艺术:世界博览会、双年展和经验美学》《孤独的视力: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和感官的官僚化》等。
2018年3至9月,在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的资助下,鲁明军前往纽约,围绕美国著名当代艺术评论杂志《十月》(OCTOBER)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从一个侧面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艺术批评与理论的历史进程,借以反思当代艺术批评、理论以及艺术媒体生态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其间,先后采访了罗莎琳·E.克劳斯、本杰明·H. D.布赫洛、伊夫-阿兰·博瓦、大卫·乔斯利特、莱耶·迪克曼等杂志编委成员和作者。本文是对卡罗琳· A.琼斯的采访,时间在2018年8月10日。 |
鲁明军(以下简称鲁):我想从2005年出版的您的一本书《孤独的视力: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和感官的官僚化》(Eyesight Alone: Clement Greenberg’s Modernism an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Senses)谈起,因为说到美国艺术评论,似乎绕不开格林伯格,自20世纪60至80年代以来,关于他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这个过程中,罗莎琳·克劳斯是一个核心人物,您怎么看当年的这个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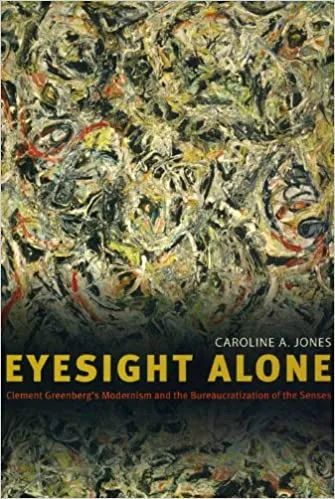
图:Eyesight Alone: Clement Greenberg’s Modernism an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Senses,2005年。
卡罗琳· A.琼斯(以下简称琼):《十月》在美国是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而且它已经与某一群担任编辑的艺术史学家联系在了一起。你可能知道,它的起源部分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莎琳·克劳斯就在我现在所在的建筑系的历史、理论与批评项目中授课。我写的关于格林伯格的《孤独的视力》这本书,所针对的就是围绕《十月》聚集起来的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团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最初与这位美国批评家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但在杂志推出后却相当积极地转而反对他。我(在《孤独的视力》中)提出的论点是,他们想批判格林伯格,以占据他的位置。所以,本质上这不是一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而是一场为权贵服务的革命。他们更想建立一套当下艺术的解释标准,以消除他们不喜欢的艺术或是他们认为没有生产力的艺术。可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像格林伯格一样,他们把这一点带到了某种极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我所谓的“现代主义范式”,文中有一个与之平行的线索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范式,然后有一场动荡的革命,随之前面的范式被后面的取代。这实际上不是科学的运作方式,这也不是艺术的运作方式。从来都没有一个干净的突破。从来也不存在单一的现代主义。总是有许多事情同时在进行,因为它是一个生态系统。对吧?
所以格林伯格和“《十月》党人”(Octoberists)——我本不打算这样说他们——他们的确陷在单一的文化中,在今天这其实是它消极的一面。当然,积极的一面是,《十月》使得艺术批评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为理论作为其写作的一部分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他们将重要的法国哲学翻译成了英文,还出版了魏玛知识分子的译本,如阿多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图:《十月》,1981年。
因此,我很荣幸能在麻省理工学院罗莎琳·克劳斯曾经所在的小组任教,当时她创办了这个杂志。在她创办《十月》的过程中,我的前同事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给她介绍了杂志的资金来源。安德森是一位建筑历史学家,他与彼得·艾森曼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克劳斯介绍给了艾森曼。于是,她向在纽约经营一家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艾森曼寻求支持,他们后来成了《十月》早期重要的赞助者。除此,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自始至今一直是《十月》的出版方或支持方。但这里,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克劳斯的合作者安妮特·米切尔森,她其实被关注和研究得非常少。
鲁:的确,在中国也很少有人提及米切尔森,一说到《十月》,大家只知道克劳斯。
琼:是的。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关键是,她并没有被看作一个“《十月》党人”,也很少被讨论和研究,但她实际上非常重要,她在巴黎时曾跟随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学习。
鲁:哦,她的学术履历里似乎没提过这一点。

图:《战舰波将金号》,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作品
琼:她把媒介研究的冷静带到了《十月》。非常重要的是,她很早就在翻译和介绍法国理论,同时她还把俄国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前卫电影带到了美国,将这一重要的知识传统联系起来,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讨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可以与那一代的新兴媒体结合起来讨论。因此,她非常重要,但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另外,挖掘克劳斯和米切尔森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米切尔森关于前卫电影的研究或许可以迁移到我们对录像艺术的理解之中。就像克劳斯说的:“录像艺术是自恋的(narcissistic)。因为录像可以同时记录和传输,所以它将艺术家的身体置于摄像机和监视器的托架之内。”所以,这里其实有一些有趣的紧张关系,可以作为艺术史探索的题目。
鲁:那其他几位呢?比如哈尔·福斯特、本杰明· 布赫洛、大卫·乔斯利特等,您觉得他们的观点和克劳斯、米切尔森差异大吗?
琼:是的,这很重要。相比其他几位,布赫洛的观点可能与我最接近,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对公开讨论“《十月》党人”还是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我对他们的批评主要还是知识层面的。当然,我也不回避对他们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性批评,在我看来他们制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集体。他们被称为“《十月》党人”其实是有原因的。如果你写劳申伯格,不引用乔纳森·D.卡茨(Jonathan D. Katz)关于劳申伯格的文章,只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十月》党人”,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冒犯。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我们需要从任意地方看作品,从任何地方理解它。
在教学中,这个圈子里也存在着一种残酷的现象。有的学生被赋予了“同龄人”的权力,他们成了教科书的共同编辑。而有的学生没有得到鼓励,被推到了圈子的边缘。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这个群体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害的。比如你看看他们的教学大纲,他们只是在互相引用,他们只是在传播对方的作品。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中文怎么说,就是你只雇用你的伙伴,叫“裙带关系”。这其实是很有腐蚀性的。它创造并维持着一种腐败的权力。说这些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立场。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尽量体现工作的智性程度,以及它所占据的权力地位。在学术实践中,我尽可能地慷慨和包容其他人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来自非精英大学的作品。比如,当我发现一本我不认识的作者的书,如果我真的很欣赏这本书,认为它很好,我会找到作者是谁,给他发电子邮件说:“哦,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的书。”然后,也许我会认识那个人,也许我们会成为朋友,进一步我也许可以得知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起学习过。我曾试图与他们成为专业同事。但我想说,我花了30年时间才被他们注意到。我记得当我在写格林伯格的书时,布赫洛邀请我参加格林伯格的会议,但其实,我们的距离也就两个地铁站,非常近。那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时刻。另外像乔斯利特,从代际划分而言,他算是我的晚辈。我其实一直关注和支持他的工作,还曾在《艺术论坛》上为他的书撰写了评论。总之,我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尽可能地慷慨和包容所有的学术研究。换句话说,我希望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地合群,所以遇到一个来自中国的正在研究《十月》的学者我很喜欢,也感到好奇——我是说,这对我来说很有趣。但这个群体本身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运作方式是:“你有多重要?我应该和你说话吗?或者我在你肩膀上看到的某人更重要……”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年轻一代是不同的。而且,我与他们的部分成员——如乔斯利特、帕梅拉·M.李、乔治·贝克等一直保持着彼此尊重的、同事般的、富有成效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一直非常钦佩哈尔·福斯特的工作,特别是他早期的工作,所以我和他成了朋友,关系也很融洽。我当然认识本杰明·布赫洛,也和伊夫-阿兰· 博瓦建立了关系——我甚至和博瓦、布赫洛“共享”一些学生,因为他们都在哈佛。只是这种关系并不对称:我会腾出手来和他们共进午餐,问他们在做什么。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投入。同样,一位非常年轻的《十月》学者在写一篇论文时,涉及了我发表的一篇论文,并善意地提到了它。她讨论了我的论文,但没有引用它。但她说:“我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任何脚注可以让人找到它,所有的脚注都是留给“《十月》党人”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但我不相信这是有意识的或形式化的,这是由他们的导师编入他们身上的一个程序:“其他人都不重要。”因此,如果你提供了一个只重视这个谱系的教学大纲,那么你就隐含地贬低了所有可能正在研究该材料的其他学者的价值。这位年轻的学者不得不接受我的论点,因为这是她所论证的核心内容。但她仍然可以通过不提供脚注来尽量弱化它。值得称赞的是,当我向她指出这一点时,她感到很尴尬和震惊。她还道歉了。因为我揭示了她被赋予的一种无意识的程序。不过我要声明的一点是,她是我的朋友,我也很欣赏她的工作,我们有时一起工作。但这是一个模式。而且对于像她这样的学生,我并不责怪,学生们都是以这种方式长大的,但我认为他们必须要解除这套程序。
鲁:刚才您也谈到,不管怎么说,《十月》在艺术界和知识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想问的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十月》在美国艺术界扮演着何种角色?
琼:其实,我非常受益于我的学生的研究,因为他们会挖掘我所经历的这些历史的一些内容。我很少去想它们,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史家,我只是在不断地向前冲。当然,《十月》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某些关键的文章,比如克劳斯关于“索引”(index)、“录像艺术”(video art)以及“立体主义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cubism)的文章都非常经典。克劳斯绝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者。除此之外,作为学生的我当时更是直接受到迈克尔·弗雷德的影响。他当时在我读本科的学校——斯坦福大学——教书,所以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形式主义方面,我认为还是非常强大的,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两者之间显然并不匹配。所以,关于艺术的想法如果不考虑社会背景,或者说只是研究这个物体中的某种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知道只有白人男子被展示意味着什么。所以,它必须与社会环境相关联。除此以外,我一直对艺术社会史也抱有强烈的兴趣。记得在我崭露头角的时候,T.J.克拉克对我影响巨大,帕特里夏· 迈纳尔迪(Patricia Mainardi)在哈佛大学教书,当时我是那里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她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还有琳达·诺克林,也正在出版、发表令人难以置信的书籍和文章。这些都是对《十月》及其新形式主义强有力的解毒剂。
因此,我现在教书的时候,通常会把这两种作家并列在一起,我会和学生谈论每一组作者论点中的利害关系。对我来说,《十月》不是唯一的影响,还有许多其他的影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一种真正的T.J.克拉克式的理论,当然它们对其他艺术史学家同样有影响。《十月》虽然有一个革命的名字,也使用了黑色、白色和红色的符号,结果却变得非政治化了。比如曾经从“《十月》党人”小组中出来的克雷格·欧文斯,他其实很重要,但当他成为一名艾滋病活动家,并试图向《十月》提出相关的问题时,却被否定了。对《十月》来说,艾滋病艺术太政治化了,它太现实了,它与社会现实有着太多的关系。所以,《十月》固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早期也有不被其范式包容的“叛逃者”。
我有个学生叫克里斯托弗·凯彻姆(Christopher Ketcham),他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极简主义和城市中的身体政治的论文。凯彻姆发现,当梅洛-庞蒂第一次被艺术家们接受的时候,是相当政治的。可是,当他在《十月》被化为艺术史的一部分时,却被去政治化了。这就相当于,一个有感觉的、移动的身体在城市中诉诸一种极简主义的表达,最终却变成了一种你在画廊里遭遇的对象,而且还没有历史。这个时候,极简主义的政治性同样被抽掉了。这非常有趣,他现在正补写历史的部分,比如当时的城市研究、城市规划和城市主义对早期极简主义者的重要影响,而这些在“《十月》党人”的叙述中被完全遮蔽了。所以,我认为那里有一种政治。这是一种什么政治呢?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在《十月》最初的几十年里,那里有政治的。那是一种非常格林伯格式的政治,一种前卫的政治,它进入了一个审美稀缺的地方,以批判资产阶级的、平庸的规范为目的。这种前卫的审美贫乏将使人们变得足够聪明,促使他们以某种方式掀起一场“革命”。格林伯格对此非常明确。但是“《十月》党人”则有点把“革命”部分推到了刊头的后面,刊头固然有黑色的字母“OCTOBER”,但他们又不希望它变得过于具体,也不希望它被讨论。所以,这只是一种革命的、政治上的刺激,实际上不会有具体的政治内容。
鲁:你觉得,《十月》的影响力减弱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是因为不能适应艺术系统本身的快速变化,还是?
琼:嗯,我觉得所有的期刊最初都是狂热的,然后渐渐降温。而且,出版本身也很难。但《十月》本身也在变化当中,其中我很欣赏的一位学者是莱耶·迪克曼—绝对的“《十月》主义者”,她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策展人,也是《十月》的编辑。我想她的加盟意味着《十月》可能要有所改变了。从此,他们也许会说:“一些非裔美国人的艺术家呢?”“一些不是‘《十月》党人’的作者呢?”迪克曼、乔斯利特这些都是克劳斯、布赫洛的学生,而这个时候其实老人们也有点累了,只好说:“好吧,随它去吧。”因此,如果他们已经在准备重塑自己,试图用一个新的形象重新宣布自己,并拒绝非政治化,这不是很好嘛?!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能,但尝试总归是必要的。
鲁:那您觉得过去这些年,通过这些尝试和努力,《十月》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琼:我不是一个关于《十月》的专家,我也不经常读它。换句话说,我也不是《十月》的跟随者。所以我没有真正的关注。此前,他们举办了一个关于“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圆桌会议,邀请我参加,这有点令人吃惊。所以我终于在《十月》上发表了文章。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改变了方向。他们当然已经催生了其他很多的杂志,如《艺术文本》(Texte zur Kunst),它在智力方面像是《十月》的附属机构。所以,我想《十月》的周围肯定有不少呼应它、模仿它的杂志。
鲁:2000年以来,互联网媒体,电子媒体的兴起,比如e-flux、《弗里兹》的模式就很不同,这也说明艺术媒体的生态包括艺术写作本身也在变化当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琼:我认为,这些都是好事,因为它们在改变生态,努力让这个生态变得更好、更丰富。
鲁:您觉得《十月》在这个生态中的位置是什么?或者说,它的目标受众是什么?
琼:我不是一个“《十月》党人”,所以这个我同样不知道。不过,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看他们写的艺术家。你知道安娜·C.查弗(Anna C. Chave)的研究吗?
鲁:没听说过。
琼:查弗关于《十月》的研究挖掘了很多历史细节。我相信很多被《十月》写到的艺术家还是受益良多,但也不可避免使个别艺术家受到伤害。我想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会后悔,他们可能会说:“我的作品并不完全是关于这个的。”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看他们写的艺术家。我能观察到的是,当罗莎琳·拉斯写到理查德· 塞拉与琼·乔纳斯(Joan Jonas)一起完成的一件艺术品时,她居然把琼·乔纳斯隐去了。在《十月》的版面上只有理查德·塞拉的名字,乔纳斯则从未被提及。当我看到这里时,整个人惊呆了。因为这件作品是他俩在一个特定空间的凝视——两个艺术家之间的凝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然后被铸造成雕塑。我的意思是,作品本身很有意义,两个相互凝视的艺术家的身体被铸成了钢。可是,在克劳斯的写作中居然漏掉了一个艺术家。这感觉就像你没有真正处理这件作品一样。即使把塞拉的身体去掉,也是在搞性别歧视。因此,我甚至不关心你是否会谈到他们的友谊或他们的关系,我关心的是,你不谈论他们所承认的关于其身体的整个实践。甚或说,你从艺术史上抹去了关于这件作品的一些东西,对吧?所以,某些艺术家的确从《十月》获益良多,但也有一些人受到了其负面影响,包括现在一些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中,我想也会有后悔者。
不过,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很乐意被《十月》写到或被提及,他们都能欣然接受,这成为其意义的一部分。比如汉斯·哈克就很喜欢布赫洛对他作品所做的分析、阐述和评论,这也成了他对自己过去的描述。而如果我说:“嗯,汉斯·哈克,看看你在1965年说了什么?”“让我们谈谈这个,让我们看看这个。”我的意思是,这真的不同。而他说:“不,不,不,那只是这个的前传。”他喜欢布赫洛为他所做的工作,乃至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做的一切。但我对那种看上去无缝衔接的故事中的空白更感兴趣,或者说我对汉斯·哈克的工作更感兴趣,特别是在他决定选择社会干预之前的工作。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成为社会干预艺术家之前是一个反人道主义者。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因此,我对艺术家早期的工作、青少年时期的工作更感兴趣,那些边缘的思维往往更令人着迷。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是关于艺术作品的那些不太整齐的叙述。
鲁:应该说是整个系统在发生大的变化,您在《全球艺术:世界博览会、双年展和经验美学》(The Global Work of Art: World’s Fairs, Biennials, and the Aesthetics of Experience)中提及,博览会、双年展、画廊业等都在塑造着全球艺术系统,但这种全球主义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来临出现了新的变化,您怎么看这种变化,或全球面临的新的危机?
琼:危机归危机,但幸运的是,艺术界的发展并没有受太大影响。人们对2008年经济衰退的反应是:“哦,好吧,艺术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把我们的钱放在那里。”所以,艺术界做得很好,双年展也做得很好。从我个人的角度看,特朗普上台以来,我的工作将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我正在写一本没有艺术内容的书,这本书是对人类世的反应。在我看来,人们正在设法通过视频将他们的身体和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与远方的观众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高度技术性的干预,他们在那里获得了甲烷泄漏的红外线,然后视频被观看一百万次。艺术界在某些方面其实是领先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落后的。我相信有一些艺术家,比如我正在关注的生物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对地球的依赖、对细菌的依赖,它们是我们90%的细胞。因此,在这些领域,我相信艺术家会领先的。但关于当前政治、关于人类世,我觉得大多艺术家只是在评论。所以他们对我现在的帮助不大。我知道我的感受,我感到绝望,我感到愤慨。我每天都能闻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惑的时刻。
现在有一种叫《每日小号》(Daily Trumpet)的东西,艺术家们每天都在投稿,画一些漫画。这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唯一能产生影响的是,我们选择无视这个人。他的整个行为的动机是分散注意力,以及对民众进行极其粗暴的操纵。因此,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忽略他,并关注实际的法律、实际的法官、实际的诉讼、实际的监管、实际的犯罪。这中间,或许只有新闻界正在发挥着作用。新闻界喜欢这种事情。所以,我不知道艺术批评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但显然,我目前正在写的艺术家都是攻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环境正义、人类世的艺术家。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所继承的问题创造了特朗普。所以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但我们也需要投票,我们需要确保其他人能够投票,我们需要停止剥夺有色人种的权利,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在真正的政治阵线上工作。而艺术界的目标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我想说的是,我在那个世界里庆祝艺术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思考那个世界。这就是我所争论的。全球主义可以是一种与全球化有关的批判性美学,我们可以尝试保持这个词,不是为了经济项目,而是为了美学反应。这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总的来说,全球艺术界是问题的一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的确是可怕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洗钱行动。当然,我肯定不是在为艺术投资公司工作。
鲁:在这样一种新的紧迫形势下,您觉得《十月》的理论局限是什么?
琼:比如,《十月》几乎没有注意到双年展,或从未将它作为专题来讨论。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或许只是市场的偶发现象。但其实无论是纽约的画廊,还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的是,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艺术世界的经验,这与艺术博物馆的保守冲动、与它的对象和稳定的保险价值及其他东西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想尝试弄清楚它。当然,当代艺术世界是由多个艺术世界组成的,而我只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只是一小部分。比如策展人,我们知道,有远见的策展人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他们一方面在制造庆祝的事件,另一方面也在诉诸历史化。
说到这里,我想起哈罗德·泽曼(Harald Szeemann),在我看来,将泽曼历史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更需要展示他是如何将当时的艺术去政治化的,以及他是如何被带入文献展,进而成为一个瑞士承包商的。他被带去中立化文献展,使其去政治化,当时那些马克思主义艺术家团体被告知,他们不再是负责人,泽曼才是负责人。所以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艺术有时会被带入一个去政治化的情境中,并且不是要永远庆祝泽曼作为一些革命者,而是要承认当时在文献展委员会的计划中他是一个反革命。所以我只是想清楚地看到他,清楚地理解他,而不是对他还抱有太过浪漫的想象。另一方面,艺术可以在政治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就在现实中,比如关于生物艺术,我的意思是,一个先驱的生物艺术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那是一个大问题,那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就在于,艺术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探索这种专有的、秘密的基因改造?艺术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事实是,他没有做基因改造,只是在做测试,向人们揭示他们的食物中有多少是经过转基因的。而联邦调查局称他为恐怖分子,你可以想见后来的事情。所以,政治有时候是非常真实的,有时它只是被艺术家鼓动起来制造的新闻。
鲁:说到艺术家制造新闻,我首先想到的是安迪·沃霍尔,您如何看沃霍尔的实践?
琼:和以往很多解释不同,我认为存在一个作为佛教徒的安迪·沃霍尔——但我不认为安迪·沃霍尔是真的佛教徒。可以用一种佛教的方式来理解重复,比如玛丽莲的重复、电椅的重复,等等。所以,我们把沃霍尔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无心之戒”(discipline of no-mind)。
鲁: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视角!
琼:是的。所以,我不认为受过“《十月》主义”训练的人会意识到,宗教实际上可能在我们的当代艺术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可能会打开我们分析问题的视野。因此,他们所写的那些艺术家往往不是这种类型的艺术家。也许有人会写伊夫·克莱因,可如果你要理解克莱因是怎么回事,就必须采取玫瑰十字教、犹太教、禅宗等所有这些疯狂的视角。当然,你会被吸引去写某些艺术家,因为他们的作品所引起的问题同样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的工作往往是找出那件作品的来源,并尝试去理解它。
鲁:没有问题了,谢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
琼:我也很开心和你聊这些问题。祝你研究顺利!

作者简介:鲁明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策展人,剩余空间艺术总监。近年策划《疆域:地缘的拓扑》(2017-2018)、《没有航标的河流,1979》(2019)、《街角、广场与蒙太奇》(2019)、《缪斯、愚公与指南针》(2020)、《惊蛰》(2021)等展览。论文见于《文艺研究》《美术研究》《二十一世紀》等刊物。近著有《目光的诗学:感知—政治—时间》(上河卓远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2020)等。2015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年获得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2017年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ACC)。同年,获得第6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2019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AAC)年度策展人奖。
©文章版权归属原创作者,如有侵权请后台联系删除